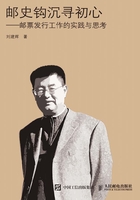
01 我的自述
北大红楼对面有一条胡同叫新开路(即现沙滩南巷),我家就在新开路的最后一个四合院里,离家五六百米的地方是我的母校27中(原孔德中学),出了校门再走五六百米就是东华门的中国邮票公司。我每天放学后有两件事,一件是去体育场打篮球,另一件就是到东华门去看邮票。
一张“梅兰芳”小型张要3块钱,相当于一般工人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我那时看着这些诱人的邮票,眼馋啊!摸摸家里给的零花钱,只能买一些盖销票,不过那时也挺满足的。令我从未想到的是,一个从四合院里走出的少年集邮者,30多年后会走上邮票发行的管理岗位。
从临危受命到亲身经历并参与世纪之交邮政体制变革的整个过程,邮票带给我痛苦,也带给我深入骨髓的热爱。有人说,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怀念另一条,而“情系方寸责所寄”大概是我对邮票感情的最好诠释,我的天平永远倾向于这一条路。
跨世纪变革
1998年3月28日,对于一向四平八稳的邮政系统来说,是一个开启变革的日子。这一天,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国家邮政局,结束了自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邮电“混”营达49年的历史。
今天来看,那是中国邮政从此走上自主经营、独立经营道路的开始,但在当时来看,那并非一条康庄大道——“以电补邮”的日子彻底告终,70万邮政员工从此要走上独立生存的艰难道路。
同年10月25日,我正式奉调到国家邮政局内设机构——邮资票品管理司就任司长。分营当口的邮政职工,普遍对前景充满忧虑:今后邮政的日子怎么过?工资收入会不会下降?各省邮电管理局的一把手几乎全部被分配到了电信部门,各省邮政的资产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90%以上的资产被分到了电信部门,80%的员工被分到了邮政系统,这意味着要用10%的资产养活80%的邮政员工,而在1997年邮电“分”营之前,邮政业务的整体收入仅占整个邮电行业的11.5%。
两极分化的现实下,原邮电部门的人千方百计挤破脑袋也要到电信去,甚至还发生过一件惨剧——1998年8月14日,就在河南省封丘县邮政局举行挂牌仪式前,即将就任的一位领导同志出于没被分配到电信部门的不满,和对邮政未来发展的本能恐惧,在凌晨四点多跳楼自杀了。
除了邮政内部的萎靡情绪,邮政外部的环境也不妙。邮资票品发行市场正深陷着四大困境:其一是香港回归时原邮电部发行的“金箔小型张”,从1997年7月1日发行时的120元钱,仅仅半年内被炒到500元人民币后开始断崖式下跌,导致“邮市亢奋期”转眼变成了“大萧条”;其二是“97”狂潮过后,邮票市场一片肃杀,市场上邮票低面值的现象卷土重来;其三是数年前欧洲、美洲等传统集邮群体大幅萎缩的阴影,在国内已悄然出现;其四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的邮政部门对邮票市场面临的形势积极进行研讨,少数对市场极其敏感的国家已经开始对邮票发行战略与策略进行调整,中国的邮票发行怎么办?
困难重重下,只有从改革和创新入手破局,而改革和创新是横在面前的一片盲区,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怎么办?我和邮资票品司的同志们,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和创新
我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全国一级市场进行调研。当接到集邮管理处汇报的邮票发行量时,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1996年和1997年的邮市狂潮引发邮票供应全面吃紧,随后扩大的发行量又遇到了1998年的市场寒冬,“供大于求”带来整个市场的票值下跌,而在国家邮政局刚刚独立运营、业务收入指标面临巨大压力之下,集邮管理处无奈做出了1999年维持邮票发行量不变的决定,看似不做减法,可以带来相应的业务收入,减轻国家邮政局开局的困境,但这对市场的打击无疑将是毁灭性的。
如果没有断臂求生的决心,整个局面将难以控制。我立刻向国家邮政局刘立清局长汇报了调研情况,局领导经过研究后决定调减发行量,我冒险提出要按500万的量进行调减,并且500万的单位不是“枚”,而是“套”,没想到却得到了肯定。这成了国家邮政局成立后邮票发行量调减的“第一刀”,并且一调就是7年。
到了2004年,我们的发行量已经从5000万套调减到1300万套,这样的调整让邮票市场真正从“供大于需”,走向“供需基本平衡”,整个市场开始回暖,当年军旅集邮家、《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刘格文写了一篇文章,叫做《2003年邮市“井喷”》,邮资票品司也概括出了邮票发行的八字经验——“宏观调控,总量适度”。
然而,这样的调整也带来了问题,发行数量的下降势必会导致收入的减少,而刚刚独立经营的国家邮政局面临巨大的收入压力。为了解决减量不减收的问题,我们摸索着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个措施就是引进“邮票个性化服务业务”,说引进,是因为这项业务并非中国邮政首创,它最早的创意者来自澳大利亚。
而真正引起我们注意的,是2001年2月在香港特区邮政署举办的新世纪第一次邮展。展会上一套“《我的祝愿》个性化邮票”边人头攒动,这款邮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性化邮票”,只是利用邮票的附票将个人的照片印上去,且现场只有一套设备,制作要花费45分钟,但这仍然不影响它成了整个展馆的热点,也让我们看到了它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巨大价值。
返京后,我们立刻召集邮票印制局和中国集邮总公司一起商讨业务方案,同年8月,“邮票个性化服务业务”在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试验并获得成功;从2002年开始,这项业务正式诞生。
但不同于中国香港地区,我们的业务不向个人开放,只面向企业、团体和学校。后者需求量大,成本低,客户稳定,大大延长了业务的成长期。一年下来,个性化邮票的定制达到了1400万~1800万版,做成集邮册之后,总收入达到7亿~8亿元,弥补了调减邮票发行量后相当一块的收入。
第二个措施是发行2003年和2004年小版邮票。这个决定跟我们到国外的考察经历相关,从1999年开始,邮资票品司陆续考察了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美国等几个国家的邮票发行部门,这些国家的集邮人数都在锐减,发行量开始大幅度下调。
但日本邮政省负责邮票的官员告诉我,他们发现在发行小版邮票时需求量会变大,于是索性把所有的大版全改成了10枚一版的小版,结果很多原本购买一两套四方连的集邮者都转去买了小版邮票。这对我的启发很大。
回国之后,我亲自监督2003年和2004年小版邮票的设计,保证它的精美度,发行之后果然受到集邮爱好者的欢迎,虽然每套只有50万~80万版的发行量,却反而提高了邮票收入。事实上,直到今天,2003年和2004年小版的市场价格仍高达三四千元人民币,“司马光砸缸”“木版年画”等精美的小版非常抢手。
第三个措施,就是分化年册发行种类和时间。每到年底,由于各省和中国集邮总公司的年册集中涌入市场,反而导致市场因承受不住而进入一年最低迷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个现象,我们开始将年册分化,一部分做成普通年册,另外一部分开发成企业形象年册。原本年会一过就成堆出现在垃圾桶中的企业宣传册,却因为其中的邮票提高了在客户手中的留存率,这样的转变备受企业欢迎,一年最多卖到了300~400万册。
同时,我们还给中国集邮总公司和各省分公司下了一道指令,每年年底,各省的邮票年册会比中国集邮总公司年册提前半个月进入市场,这就缓解了集邮总公司年册对各省年册的冲击,销售的节奏把市场真正变成了我们可以调剂的窗口。
这三个措施在减量的情况下,平稳了市场,保证了收入,让邮政部门慢慢度过了寒冬。
“外脑”诞生
回想起在任期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除了在经营层面进行改革和创新,邮资票品司还在发行的两个重要环节——邮票选题的遴选和邮票图稿的审议方面进行了改革。
从国家邮政局成立的第二年开始,两个“外脑”相继亮相,一个是“国家邮政局邮票选题咨询委员会”,另一个是“国家邮政局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前者的职能重在“咨询”,后者重在“评议”。
国家邮政局拟列入选题规划或发行计划的所有选题,都要经过“选题咨询委员会”的把关,请这些涵盖我国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评头论足”,对一些拿不准的选题也请他们提出看法,以便定夺。
之所以想要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是因为一个被集邮者诟病多年的问题。在调来邮资票品司任职之前,我曾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工作过五个年头,对于广大集邮者和集邮协会的专职干部所思所想有一定了解。当时集邮者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新邮发行的当天,窗口不能“按时足量”供应,往往要过一段时间,集邮门市部才有出售,影响了邮友们邮寄“首日封”的时间,也使邮政的信誉受到损害。
经过调研,尽管原因很多,但根本症结就出在选题上,选题的滞后下达,影响了图稿设计,后者又直接影响到印刷环节,邮票厂整天加班,也赶不上发行日。于是,我们将邮票选题下达时间从“一年一下”调整为“一下三年”,三年的图稿一起组织设计,很多特种邮票、纪念邮票没有时间限制,哪套图稿设计成熟就先安排哪套发行。这样一来,生产就主动了。2001年,困扰多年的邮票发行不能“按时足量”供应各个集邮门市部的顽疾,终于得到了解决。
另一个“外脑”——“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的成立时间要早于“选题咨询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中国邮票把关,委员会除了第一任主任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还汇集了袁运甫、杜大凯、谭平、吴山明、徐启雄、董纯琦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和印刷专家,从组建第一天起,所有请评委评议的图稿都会隐去作者姓名,同时,对评议的过程和结果,既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能私自向外界透露,会议高度民主,在评议图稿时对作品的优劣、质量的高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听这些卓有成就的艺术家评稿,就如同接受一次文化的洗礼。从中国美术的方向到当前存在的问题,每个人襟怀坦荡、虚怀若谷、言辞尖锐、语言幽默,它虽然不是决策机构,但经“外脑”评议和推荐的图稿,使国家邮政局决策时心中有了底,为国家邮政局的最终定夺提供了参考。这些公平、公正的评议,也使那些“滥竽充数”“走门子”“走关系”者哑口无言,无地自容。
这两个委员会对中国邮票的发行工作和图稿设计水平的提高,的确做出了重大贡献。
永不离开
最近几年,从纪录片《中国珍邮》的策划、撰稿、改稿、审稿、审片,到石家庄邮政专科学院每学期24课时的授课,参与南宁亚洲邮展相关策划工作以及品鉴会、研讨会,以及连篇累牍的约稿、写稿等,种种琐碎事情已经压扁了我的时空。
对邮票和集邮深入骨髓的热爱,成为近两年已不在一线工作的我仍然不断出现在邮票发行和集邮活动之中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离开了工作岗位,我才真正有精力为我热爱的邮票事业做一些事情。
如果说有什么不得不做的事情,那么制作《中国珍邮》算是其中一件,通过这样一部纪录片来展现我国各个时期的珍贵邮票,是我酝酿了十几年的想法。
引发这个想法的,是1999年“中国1999世界集邮展览”上的一个插曲,那是中国首次举办综合性世界邮展,有两枚珍邮参展,其中一枚是红印花小字“当壹圆”四方连,另一枚是大龙阔边五分银全张,两枚都是孤品,由香港著名集邮家林文琰先生收藏。
这两件珍邮价值高昂,前者在20世纪80年代时的转让价就已高达30万美金,而后者于1991年在英国索斯比拍出了37.4万英镑的高价,平时一直保存在汇丰银行的金库里。
参展邮票要从香港汇丰银行运到启德机场,慎重起见,林文琰先生想要为邮票买1000万港币的保险,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花销,我们没有这笔经费。但是为了两件国宝的安全,保卫组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安全保卫方案,由公安部八局全程将邮票从机场护送到展场,展览期间也采取了多种安保措施。
邮展期间,我代表组委会请林文琰夫妇吃饭,他们讲述了几代集邮家如何不懈努力,最终把流失到海外的国宝请回到中国来,其中“大龙阔边五分银全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一位美国集邮家施塔少校收藏,他同时还是美国华邮协会的会长,直到1991年邮票才被林文琰先生拍回到祖国。
中国集邮家的美德、爱国情操让我非常感动,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拍一部电视片,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直到2012年10月,我把中国珍邮搬上荧屏的想法遇到了知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新闻中心影视部的陶汪澎和我一起,花了3个月的时间将4集样片制作完成,报批通过后,我找来李近朱、李毅民、林轩等集邮家,共同做了一个文案。目前策划中的20多部均已拍摄完成,其中6部已经分别于2016年3月20和21日播出,每天3集。不到一个月,就在央视网达到超过1000万次的点击量,这个片子还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优秀原创网络电视节目(非剧情类)”。
截至目前,我一共为邮政拍了三部影视作品:一部是1991年在央视播出的10集电视系列片《国脉所系》,在次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全国电视片评选中荣获电视系列片二等奖;一部是1999年为举办“中国1999世界集邮展览”而拍摄的20集电视连续剧《绿衣红娘》,成为邮政部门组织拍摄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再一部就是《中国珍邮》,这些在邮政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的命运始终和邮政是在一起的,让更多人了解中国邮政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这应该是一个老邮政人卸不掉的责任。(作者口述,董琪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