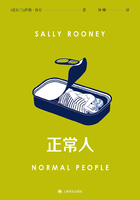
第6章 两天后(2011年4月)
他站在病床边,他母亲去找护士了。你就穿这么点儿吗?他外婆说。
什么?康奈尔说。
你就穿这么一件毛衣吗?
哦,对,他说。
这天早上康奈尔的外婆在奥乐齐超市的停车场滑倒了,摔坏了髋关节。她比其他病人都年轻,才五十八岁。康奈尔记得,玛丽安的母亲也是五十八岁。总之,他外婆的髋关节似乎情况不妙,可能骨折了,于是需要康奈尔开车载洛兰去斯莱戈镇上的医院看望她。病房另一头的床上有人在咳嗽。
我还行,他说,外面挺暖和。
他外婆叹了口气,仿佛他对天气的评价让她痛苦。大概的确如此,因为他做的一切都让她痛苦,因为她恨他还活着。她挑剔地上下打量着他。
好吧,你显然一点都没有遗传到你妈,是不是?
对,的确没有,他说。
洛兰和康奈尔的外貌是两种类型。洛兰一头金发,面容柔和,没有棱角。他的男同学们都觉得她很漂亮,也常跟康奈尔这么说。她大概真的很漂亮,那又怎样,他不觉得被冒犯。康奈尔的头发是深色的,脸轮廓分明,像一幅罪犯的肖像画。不过,他知道他外婆之意不在外貌,而是暗指他父亲的身份。所以,好吧,对此他无话可说。
除洛兰之外没人知道康奈尔的生父是谁。她说他什么时候想问了就可以问,但他真的不在乎。晚上出去玩时,他朋友有时会提起他父亲,好像这个话题很深刻很有意义,只有喝醉了才能聊。康奈尔觉得这很压抑。他从未想过那个让洛兰怀孕的男人,他干吗要去想他?他的朋友们好像非常执迷于自己的父亲,要不就模仿他们,要不就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努力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和父亲发生争执时,总是表面上争的是一回事,底下还藏着一层隐秘的意义。康奈尔和洛兰吵架往往是为了扔在沙发上的一条湿毛巾,仅此而已,真的就只是关于那条毛巾,最多再关于康奈尔是不是有粗心大意的毛病,他希望洛兰不要因为他乱扔毛巾就认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而洛兰说如果他真的想被视作一个负责的人,就应该在行动上表现出来,诸如此类。
二月底,他开车载洛兰去票亭投票,路上她问他要投给谁。某个独立党候选人,他含混地说。她笑了。让我来猜,她说,共产党员德克兰·布里。康奈尔没理她,继续看路。他说,要我说,这个国家需要一点共产主义。透过眼角他能看见洛兰在微笑。她说,得了吧,同志。我才是那个给你灌输良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人,你忘了?洛兰的确有价值观。她对古巴感兴趣,也关注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最后康奈尔的确投给了德克兰·布里,他在第五轮时[7]被淘汰了。三个席位里有两个最终落在爱尔兰统一党[8],剩下那个归于新芬党[9]。洛兰说这简直是个耻辱。就是换了群罪犯,她说。他发短信给玛丽安:爱统当选了,我操。玛丽安回道:佛朗哥之党[10]。康奈尔还得去查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玛丽安说她觉得他长成了一个好人。她说他很友善,人人都喜欢他。他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她这句话。想这句话让他很愉悦。你是个好人,大家都喜欢你。为了考验自己,他会努力不去想它,然后再来想它,看它是不是还让他感到愉悦,的确如此。不知为何他希望自己能把玛丽安这句话说给洛兰听。他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能让洛兰安心,但是对什么感到安心呢?她儿子不是个一无是处的人?她没有浪费自己的人生?
我听说你要去圣三一大学,他外婆说。
嗯,要是我分够的话。
你怎么惦记上圣三一了?
他耸耸肩。她笑了,带着嘲讽。哦,对你来说算不错了,她说,你要去学什么?
康奈尔克制住自己,没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看时间。英文系,他说。得知他第一志愿填了圣三一,他的舅舅舅妈都大为赞叹,这让他有点尴尬。要是他真的被录取了,他有资格申请全额生活费补助金,但是就算有补助金,他也必须在夏天全职打工,学期中至少也得做兼职。洛兰说她不希望他上大学时打太多工,希望他能专心读书。这让他很内疚,因为英文系不是能让你找到工作的那种“货真价实”的学位,它不过是个笑话,于是他觉得自己说不定真的应该报法律系。
洛兰回到病房。她的鞋在瓷砖上发出单调的啪嗒声。她跟外婆聊起休假去了的会诊医生、奥马利医生,还有X光片的事。她很仔细地向外婆转达了这些信息,把最重要的事写在一页笔记本纸上。最后,外婆亲了亲康奈尔的脸,他便和洛兰一道离开了。他在走廊里用洗手液消毒,洛兰在一旁等他。然后他们走下楼梯,走出医院,来到明亮、湿濡的阳光当中。
那天晚上筹款会后,玛丽安把她家的事告诉了他。他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跟她说他爱她。他就那么说了出来,就像你要是摸了什么烫的东西,会把手抽回来一样。她当时在哭,他说话时没过脑子。他真的爱她吗?他对爱情了解得太少,不知道答案。一开始他觉得这肯定是真的,既然他说了这话,他干吗要撒谎?但他又记起自己有时的确会撒谎,哪怕没有打算或没有缘由说谎。这不是他第一次想告诉玛丽安他爱她,不管这是真是假,但这是他第一次屈服于这种冲动,说出了口。他注意到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回答,她的迟疑让他介意,仿佛她可能不会有所回应一样,当她回应之后他感觉好多了,但或许这并不代表什么。康奈尔希望自己知道别人私下里是怎么生活的,这样他就能模仿他们。
第二天早上,他们被洛兰插钥匙进锁孔的声音吵醒。外面很亮,他的嘴很干,玛丽安已经坐了起来,在穿衣服。她一味地说,对不起,不好意思。他们肯定稀里糊涂睡过去了,他原本打算昨晚送她回家的。她穿上鞋,他也穿上了衣服。他们下楼时看见洛兰站在走廊里,提着两塑料袋的蔬果杂货。玛丽安穿着前一天晚上的裙子,那条吊带黑裙。
你好,亲爱的,洛兰说。
玛丽安的脸红得像只灯泡。不好意思打扰了,她说。
康奈尔没有碰她,也没跟她说话。他胸口疼。她走出前门,一面说,再见,不好意思,谢了,对不起。还没等他下楼梯,她就把门在身后关上了。
洛兰抿着嘴,像在努力憋住笑。你来帮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她说。她把其中一个袋子递给他。他跟着她进了厨房,看都没看就把那袋东西放在桌上。他揉着脖子,看她把东西从袋子里拿出来,收拾归位。
有什么好笑的?他说。
她没必要看我回来了就那样溜掉,洛兰说,我很高兴看到她,你知道我很喜欢玛丽安。
他看着母亲把能再利用的塑料袋折了起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她说。
他闭上眼睛,过了几秒后睁开。他耸了耸肩。
我知道有人下午会来我们家,洛兰说,而且我又在她家干活,你懂的。
他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你肯定真的很喜欢她,洛兰说。
为什么这么说?
你不是为这个才去圣三一的吗?
他把脸埋进手里。洛兰笑出声来,他听见了。你现在搞得我不想去了,他说。
哦,得了吧。
他的手探进刚才放在桌上的那袋东西,拿出一包干的细意面。他不自在地把它拿到冰箱边的柜子里,和其他意面放在一起。
所以玛丽安是你女朋友喽?洛兰问。
不是。
什么意思?你跟她上床但她不是你女朋友?
你在窥探我的隐私,他说,我不喜欢,这不关你的事。
他回到那袋东西边,拿出一盒鸡蛋,把它放在灶台上的葵花籽油旁边。
是因为她母亲吗?洛兰说,你觉得她会嫌弃你?
什么?
她可能会嫌弃你,你知道的。
嫌弃我?康奈尔说,莫名其妙。我做什么了?
我认为她可能会觉得我们跟她不是一个阶层的。
他越过厨房瞪着他母亲,看她把一盒超市自有品牌的玉米片放进柜子里。他之前从没想过玛丽安家会自认为比他和洛兰高一等,会不屑于和他们打交道。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念头让他愤怒。
怎么,她觉得我们配不上他们?他说。
不知道。我们或许会知道答案。
她不介意你给她家做卫生,却不喜欢你儿子和她女儿一起玩?太搞笑了。这简直像十九世纪的观念,简直让我发笑。
你听起来不像在笑,洛兰说。
相信我,我在笑。太搞笑了。
洛兰合上柜子,转过身好奇地看着他。
那你这么遮遮掩掩干吗?她说,如果不是因为她母亲丹尼丝·谢里登的话,难道说玛丽安有男朋友,你不想让他发现?
你这些问题越来越侵犯个人隐私了。
这么说她的确有男朋友喽。
没有,他说,我不会再回答你问题了。
洛兰扬了扬眉毛,什么也没说。
他把空塑料袋放在桌上,然后停下来,手里揉着袋子。
你不会跟别人说的吧?他问。
越听越不对劲。我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说?
他硬下心肠,答道,因为对你没好处,反而会给我惹很多麻烦。他想了想,又狡猾地补充道,对玛丽安也是。
哦天哪,洛兰说,我觉得我都不想知道。
他继续等着,因为她还没有明确承诺会保密,最后她恼怒地举起双手,说,我多得是比你的性生活有趣的东西可以八卦,行了吧?别担心了。
于是他上了楼,坐到床上。他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他就那么坐着。他想着玛丽安的家人,想着自己配不上她,还想着她前一天晚上跟他讲的事。学校里有些男生说过,有时女生会编故事来博眼球,说她们有过很惨的遭遇之类的。玛丽安跟他讲的故事的确挺博眼球的,她说小时候她爸会打她,而且她爸已经死了,所以他没法为自己辩白。康奈尔知道玛丽安有可能为了博得同情而撒谎,但他也知道,无比清楚地知道,她并没有撒谎。他甚至觉得她没有告诉他实情究竟有多糟。成为这件事的知情者,以这种方式和她相连,让他有点不安。
那是昨天的事了。今早他和往常一样提前到校,往储物柜里放书时,罗布和埃里克开始冲他装模作样地欢呼。他把包扔在地上,没理他们。埃里克把一只胳膊甩在他肩膀上,说:来啊,跟我们交代了。你那天晚上得手了吗?康奈尔从裤兜里摸出储物柜钥匙,把埃里克的胳膊从他肩上抖开。好笑得很,他说。
我听说你们一起离开时看起来很亲密,罗布说。
发生点什么了吗?埃里克说,老实讲。
没有,当然没有,康奈尔说。
为什么是当然?雷切尔问,大家都知道她喜欢你。
雷切尔坐在窗沿上,穿着半透明黑丝袜的腿缓慢地来回摆动。康奈尔没有和她对视。莉萨靠着储物柜坐在地板上写作业。卡伦还没来。他希望卡伦快点进来。
我敢打赌他来了发爽的,罗布说,他从来都不跟我们讲。
我不会为此而瞧不起你的,埃里克说,她打扮一下还不算丑。
没错,她只是脑子有问题,雷切尔说。
康奈尔假装在储物柜里找东西。他的双手和衣领下面开始冒出白色薄汗。
你们太毒了,莉萨说,她做什么惹到你们了?
问题是她对沃尔德伦做了什么,埃里克说,瞧他躲进储物柜那样子。快说,扭捏什么。你舌吻她了吗?
没有,他说。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莉萨说。
我也觉得,埃里克说,我觉得你应该补偿她,康奈尔。我觉得你应该邀请她去毕业舞会。
他们都爆笑起来。康奈尔关上储物柜,右手有气无力地提着书包,走了出去。他听到他们在喊他,但他没有转身。进厕所后他把自己关进小隔间里。黄色的墙向他压来,他脸上沾满了汗。他不停地想自己在床上对玛丽安说的话:我爱你。这太可怕了,感觉就像透过闭路电视,看着自己犯下一桩可怕的罪行。她一会儿就要来学校了,她会一面把书装进书包里,一面自顾自地微笑,对一切浑然不觉。你是个好人,大家都喜欢你。他极其不适地深吸一口气,然后吐了。
从医院开车出来,他打上左转灯,回到国道N16上。他的眼底很疼。他们沿着商场行驶,两旁是一排排深色树木。
你还好吧?洛兰问。
嗯。
你脸色不太好。
他吸了口气,吸得安全带有点勒到肋骨了,然后呼气。
我邀请雷切尔去毕业舞会了,他说。
什么?
我邀请雷切尔·莫兰跟我一起去毕业舞会。
他们刚好快要经过一个加油站,洛兰快速地拍拍车窗,说,在这儿停车。康奈尔转过头,一脸疑惑。什么?他问。她又拍了拍车窗,这次更用力,指甲在玻璃上嗒嗒响。停车,她又说了一次。他迅速打上右转灯,检查后视镜,然后靠路边停了下来。加油站旁有人拿着水管在冲一辆货车,水淌下来,聚成一道道深色水流。
你要去买什么东西吗?他问。
玛丽安跟谁一起去毕业舞会?
康奈尔心不在焉地攥着方向盘。我不知道,他说,你让我在这儿停下来,不是就为了跟我讨论这个吧?
所以可能不会有人邀请她,洛兰说,于是她根本就不会去。
嗯,或许吧。我不知道。
这天吃完午饭回教室的路上,他走在队伍后面。他知道雷切尔会看见他,然后在前面等他,他知道的。等她真的这么做了,他的双眼几乎紧紧闭上,眼前世界一片灰白,然后问道,嗯,有人邀请你去毕业舞会了吗?她说没有。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好吧,她说,不过我得说,我原本期待你能问得更浪漫一点。他没回答,因为他觉得自己仿佛刚从高耸的悬崖上跳了下去,摔死了。他很高兴自己死了,他也不想活了。
玛丽安知道你要带别人去吗?洛兰问。
还没。我会跟她讲的。
洛兰的手盖在嘴上,他看不出她是什么表情。她可能感到惊讶、担忧,或者快要吐了。
你没想过你应该邀请她?她问,毕竟你每天放学都操她。
别说得这么难听。
洛兰吸气时鼻孔都发白了。那你想让我用什么词?她问,我是不是该说你利用她,把她当炮友,这样说是不是更准确?
你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没有谁在利用谁。
你是怎么让她保密的?你是不是跟她讲,她要是说出来不会有好下场?
老天,他说,当然没有。这是双方同意的,好吧?你太小题大作了。
洛兰自顾自地点着头,透过挡风玻璃往外看。他紧张地等她重新开口。
你同学不喜欢她,是不是?洛兰问,我猜你是怕他们要是发现了,会怎么说你。
他没有回答。
好吧,那让我来告诉你,我会怎么说你,洛兰说,我觉得你是我的耻辱。我为你感到羞耻。
他拿袖口擦了擦额头,说,洛兰。
她打开副驾侧的门。
你要去哪儿?他问。
我搭公车回家。
你在说什么啊?正常一点,好不好?
我要是待在车里,只会说些让我后悔的话。
这话什么意思?你干吗在乎我跟谁去不跟谁去啊?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她大力推开车门,下了车。你的反应太奇怪了,他说。作为回应,她把门狠狠地甩上。他痛苦地攥紧方向盘,但没说话。他本可以说,这他妈的是我的车!我说过你可以甩门了吗,啊?洛兰已经往前走了,她每跨一步,手提包就打在她的胯上。他看着她在转角拐弯。为了买这辆车,他放学后在加油站打了两年半的工,就为了载他母亲,因为她没有驾照。他现在其实可以跟在她后面,把车窗摇下来,喊她上车。他几乎想这么做了,但她不会理睬她。于是他坐在驾驶座上,头靠上头枕,听着自己愚蠢的呼吸声。加油站里,一只乌鸦啄着一只被扔掉的薯片口袋。一家人从便利店里出来,手里拿着冰激凌。汽油的味道充斥着车内的空气,沉甸甸的,像头疼的感觉。他重新发动了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