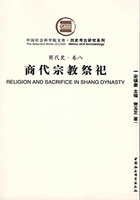
第二节 商人宗教的起源——图腾崇拜的遗迹
pgge:6-25
历史上的商王朝是由成汤灭掉夏桀后开始的。据史书记载和与殷墟甲骨文互证,目前已知商人在成汤以前还经历了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王亥)—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十三世祖先,这是以男性祖先的世次记录的商族人的世系。因此契是商族人记忆中的第一位男性祖先,是商族人进入原始社会中的父系氏族社会后的第一位首领,可以说契是商族人的始祖。据《史记·殷本纪》等古书记载,契是由其母简狄吞食玄鸟卵受孕而生的。(详下文)
迄今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原始氏族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即它在原始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的初期就已经产生了。这就告诉我们,商族人的宗教在契以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
在原始氏族社会中,“人类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不仅不可能把与自己生存攸关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作为支配的对象,而且反把它们当作支配自己生存和生活的神秘力量。这两种力量就在原始人的观念中表现为对超自然的自然力量和对超人间的氏族祖先的崇拜,这两种宗教观念是原始宗教的基本观念,由此观念而象征化为两种基本的崇拜对象。”[2]换句话说,这两种基本的崇拜对象就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而图腾崇拜正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一种最古老的宗教崇拜形式。因此我们认为“图腾论”应该是最接近人类宗教起源的理论。
什么是图腾?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叙述“图腾”二字的来历说,“图腾(totem)”一词是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氏族的方言,“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3]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还处在蒙昧无知的阶段,人们对人与自然物的界限还是模糊和朦胧未分的,这使得他们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一种动物、植物或某一种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认为这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就是自己氏族的祖先,他们把它称之为自己氏族的图腾,认为它是自己氏族的保护神,从而对其崇拜,并用它作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就是图腾崇拜。有学者说:“图腾崇拜本质上是氏族制度在宗教上的表现,它既是宗教体制,又是社会制度。”[4]这是十分正确的。如果用吕大吉先生关于宗教的四要素和关于宗教的定义来考察,那么,图腾崇拜应该是人类最早的宗教形式,也即图腾崇拜应是人类宗教的起源。
中外民族学的大量材料既证明了图腾崇拜是随着原始氏族制的产生而产生的,又证明了在古代世界的各民族中几乎都发生过图腾崇拜。在美洲、澳洲、亚洲、非洲、欧洲各大洲都曾发生过图腾崇拜。摩尔根等学者曾举出过世界不少民族的图腾名称,如:北美洲的辛尼加部落的八个氏族分别以狼、熊、龟、海狸、鹿、鹬、鹭、鹰八种动物为图腾;澳大利亚的卡米拉罗依部落分为六个氏族,它们分别以鬣蜥、袋鼠、负鼠、鸸鹋、袋狸、黑蛇为图腾;南非洲的贝川那人分为鳄族、鱼族、猴族、水牛族、象族、豪猪、狮族、藤族等八个氏族[5]。在我国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远古图腾的传说记录,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有:“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这里的“云”、“火”、“水”、“龙”、“凤鸟”、“玄鸟”等都是氏族的图腾标志。就是到了近代,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还保留有图腾的痕迹,如云南的傈僳族就存在着图腾制度的残余,“傈僳族在怒江地区内有十几个氏族,即:蜡饶息(虎)、阿吃息(羊)、吉饶息(蜂)、鹅饶息(鱼)、汗饶息(鼠)、明饶息(猴)、业饶息(雀)、乌饶息(熊)、麻打息(竹)、括饶息又称木必息(荞)。其中以木必息人数最多。这些姓氏可能是原始氏族的‘图腾’”[6]。又如怒族,也有图腾制度的残余。这里就不列举了。
那么,远古时期的商氏族又是以什么为图腾的呢?
宗教学家吕大吉先生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图腾崇拜逐渐淡薄,但其残余信仰仍然存在”[7],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从后世的古文献中,从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可以找到远古时期商氏族图腾崇拜的遗迹。前辈学者曾根据这些记载来论证过远古时期的商氏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
胡厚宣先生曾经把文献中记载的商人以玄鸟为图腾的资料按时代先后做了分类[8],这里我们对胡先生的分类稍作调整并做某些删节,对胡先生的某些引文做了变动,对其个别引误之处做了纠正,再录之于下:
1.《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笺:“天使 下而生商者,谓
下而生商者,谓 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2.《诗经·商颂·长发》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玄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 卵而生契。”
卵而生契。”
这两条是说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出商人的始祖契。这是时代最早的关于玄鸟生商的传说。
3.《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诱注曰:“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
这里是说有娀氏有两个女儿。
4.《楚辞·离骚》说:“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王逸注曰:“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
5.《离骚》又曰:“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曰:“高辛,帝喾有天下号也。”
6.《楚辞·天问》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9]。”王逸注曰:“简狄,帝喾之妃也。玄鸟,燕也。贻,遗也。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7.《九章·思美人》说:“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王逸注曰:“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
胡先生说:“《离骚》《天问》《思美人》,都是战国时屈原所作。这时的简狄,已经成了帝喾之妃,而商的始祖契,就有了父亲了。”[10]
这种传说到了秦汉时期,就成了简狄是在行浴时吞吃的鸟卵。如:
8.《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9.《尚书·中侯》说:“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尚书·中侯》)
后来,这一传说又有了变化:
10.《吕氏春秋·仲春纪》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高诱注曰:“王者后妃以玄鸟至日,祈继嗣于高禖。”
11.《礼记·月令》之说与《吕氏春秋·仲春纪》之说相同。郑玄注《月令》说:“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12.《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传说:“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对于古文献中玄鸟生商的记载,胡厚宣先生总结说,是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地有所变化的。不过,“这些传说,虽然有详有略,逐渐演变,或有不同,但说商朝的始祖契,是由玄鸟而生,这一点,则无论如何,始终还是一致的。”[11]这是十分正确的。在早期的作品《诗经》中契没有父,到了后期战国时代的屈原就在其作品中给契增加了个父,这以后的汉代作品也就跟其所言了。
对于古文献中玄鸟生商的传说,两千多年来的传统史学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今天,我们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古代历史,就可以知道,玄鸟生商的传说,一是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商氏族,曾经经历过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二是说明远古时期的商氏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这就是说,商人记忆中的第一位男性祖先契,是由有娀氏族的女性简狄(知其母)与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的男性(不知其父)交媾而生的。
商人以玄鸟为图腾的遗迹不仅存在于古文献的记载中,而且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有遗迹可寻。
最早是于省吾先生从商代金文中找到了商人鸟图腾的证据。
1959年,于先生发表《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一文[12]。在该文中,于先生举出商代铜器“玄鸟妇壶”铭文来论证商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

图1—1 “玄鸟妇” 壶铭
(《三代》12·2·1)
“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个字合书的铭文(《三代》12·2·1。图1—1)。于先生说:“玄鸟妇三字系合书,玄字作‘ ’,金文习见,右侧鸟形象双翅展飞。”“壶铭既为玄鸟妇三字合文,它的含义,是作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再就壶的形制环玮和纹饰精美考之,可以判定此妇既为简狄的后裔,又属商代的贵族,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玄鸟妇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图绘文字,它象征着作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后裔是很显明的。”于先生还论证了“玄鸟妇”不为妇名的理由。他说:“有人认为商代金文每称某妇,妇上一字当为妇名,这是不对的。商器如比作‘伯妇簋’,‘中妇鼎’,伯、中系行次。又如‘商妇甗’,‘齐妇鬲’,‘杞妇卣’,妇上一字为部落名或地名。又如‘妇
’,金文习见,右侧鸟形象双翅展飞。”“壶铭既为玄鸟妇三字合文,它的含义,是作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再就壶的形制环玮和纹饰精美考之,可以判定此妇既为简狄的后裔,又属商代的贵族,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玄鸟妇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图绘文字,它象征着作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后裔是很显明的。”于先生还论证了“玄鸟妇”不为妇名的理由。他说:“有人认为商代金文每称某妇,妇上一字当为妇名,这是不对的。商器如比作‘伯妇簋’,‘中妇鼎’,伯、中系行次。又如‘商妇甗’,‘齐妇鬲’,‘杞妇卣’,妇上一字为部落名或地名。又如‘妇 卣’,‘妇己簋’,
卣’,‘妇己簋’, 为妇名,己为庙号。又如周器‘王妇
为妇名,己为庙号。又如周器‘王妇 孟姜匜’,‘邛君妇龢壶’,妇上冠以王和邛君,在文法上都是领格,指某人而言,妇下一字为妇名。可证凡属妇名都在妇字之下。再以卜辞证之,早期卜辞称妇(婦字本作帚,稍晚则从女作婦)某者习见,妇下一字都是妇的名或姓,如妇好,妇妌,妇良等,名与姓无在妇上者。另外也有角妇(粹一二四四)、雷妇(后下四二·七)二例,何以不称为妇角与妇雷,这也是研契诸家所不解者。按角与雷均系商王同族的臣僚……可见角妇是角的妇(古人称妻为妇)而雷妇是雷的妇,与商王的多妇都称为妇某者迥然有别。以上所说,就足以证明玄鸟妇的玄鸟二字并非妇名,它系商人先世图腾的残余是没有疑问的。”除此之外,他还举出下版卜辞以证明古文献中的有娀氏:
孟姜匜’,‘邛君妇龢壶’,妇上冠以王和邛君,在文法上都是领格,指某人而言,妇下一字为妇名。可证凡属妇名都在妇字之下。再以卜辞证之,早期卜辞称妇(婦字本作帚,稍晚则从女作婦)某者习见,妇下一字都是妇的名或姓,如妇好,妇妌,妇良等,名与姓无在妇上者。另外也有角妇(粹一二四四)、雷妇(后下四二·七)二例,何以不称为妇角与妇雷,这也是研契诸家所不解者。按角与雷均系商王同族的臣僚……可见角妇是角的妇(古人称妻为妇)而雷妇是雷的妇,与商王的多妇都称为妇某者迥然有别。以上所说,就足以证明玄鸟妇的玄鸟二字并非妇名,它系商人先世图腾的残余是没有疑问的。”除此之外,他还举出下版卜辞以证明古文献中的有娀氏:
□辰王卜,在兮[贞]: 毓
毓 。[王]占曰:吉。在三月。(《前》2·11·3,《合集》38244,五期)
。[王]占曰:吉。在三月。(《前》2·11·3,《合集》38244,五期)
这是一条第五期卜辞,卜问 氏女生育之事。于先生引辞不太确切,今重引如上。于先生说:“
氏女生育之事。于先生引辞不太确切,今重引如上。于先生说:“ 即娀,有娀氏即有戎氏,晚期商王娶戎女为妇,因而加女旁称之为娀,犹之乎商王娶羌女为妇,因而加女旁称之曰姜(姜
即娀,有娀氏即有戎氏,晚期商王娶戎女为妇,因而加女旁称之为娀,犹之乎商王娶羌女为妇,因而加女旁称之曰姜(姜 见乙中五四○五)。由此可见,商代从先世契母简狄一直到乙辛时期还与有娀氏保持着婚媾关系。”
见乙中五四○五)。由此可见,商代从先世契母简狄一直到乙辛时期还与有娀氏保持着婚媾关系。”
于先生总结说:“根据上面的论证,有娀氏之娀,既见于殷虚卜辞,而玄鸟为图腾又见于商代金文,这是文献记录已与地下史料得到了交验互证。足征《诗》篇所咏,《天问》所疑,其来有自。”
受于省吾先生《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一文的启发,胡厚宣先生在1964、1977年先后发表了《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两文[13],从商代甲骨文中找到了远古商氏族鸟图腾的证据。这些证据共是十条卜辞,分刻在八版甲骨上。下面我们再征引这些卜辞并做进一步诠释。这些卜辞是:
(1)其告于高祖王亥三牛。
其五牛。(《合集》30447,《宁》1·141,《京津》3926,三期。图1—2)
这是一版牛胛骨刻辞,属于第三期。卜辞有两问,先问告祭于高祖王亥用三头牛好吗,再问还是用五头牛好呢。“告”祭即祷告之意。辞中王亥之“亥”字,从亥,从又持鸟,作“ ”形,即作用手捉鸟形。
”形,即作用手捉鸟形。
(2)□□卜,王[贞]:其燎[于]上甲父[王]亥。(《合集》24975,《虚》738,二期。图1—3)
这是一版第二期龟腹甲刻辞。由商王亲自贞问,问燎祭上甲的父亲王亥一事。“燎”之义,《吕氏春秋·季冬纪》说:“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高诱注:“燎者,积聚柴薪,置璧与牲于上而燎之,升其烟气。”即“燎”之意为烧,甲骨文的燎字正像积柴而燃之形。该辞中王亥之“亥”,从亥,从鸟,作“ ”形。
”形。

图1—2 祭祀王亥,亥字作鸟形
(《合集》30447)

图1—3 祭祀王亥,亥字作鸟形
(《合集》24975)
(3)辛巳卜,贞:来辛卯酒河十牛,卯十牢。王亥燎十牛,卯十牢。上甲燎十牛,卯十牢。
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宗于河。(《屯南》1116,四期。图1—4)
(4)辛巳卜,贞:来[辛卯]……王亥燎十……(《合集》34293,《安明》2309,四期。图1—5)
(5)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于河。
[辛]巳卜,[贞]:王[亥]……河。(《合集》34294,《佚》888,四期。图1—6)

图1—4 祭祀王亥、河、上甲,亥字作鸟形
(《屯南》1116)

图1—5 祭祀王亥,亥字作鸟形
(《合集》34293)

图1—6 祭祀王亥、河、上甲,亥字作鸟形
(《合集》34294)
以上三版均是刻在牛胛骨上的第四期卜辞。三版上的五条辞皆是于辛巳日卜问的。第(3)版上有两辞,第一辞于辛巳日卜问在未来第十天的辛卯日,用十头牛、并“卯十牢”来祭祀先公河,用燎十头牛、并“卯十牢”来祭祀先公王亥,用燎十头牛、并“卯十牢”来祭祀先公上甲,先公河、王亥、上甲所受祭礼相同。其中的“酒”字,当是指祭祀之意[14]。“卯”在卜辞中除借为地支字外,多为用牲之法,郭沫若先生说:“因卯之字形取义,盖言对剖也。”[15]即卯为剖杀之意。卜辞中的“卯”字作为用牲之法时,多施用于牛、羊牲,有时也施用于人牲。“牢”之所指,学者有歧意。《诗经·瓠叶·序》郑笺:“繫养者曰牢”。《周礼·牧人》:“凡祭祀,共其牺牲,以授充人繫之。”郑注:“授充人者,当殊养之。”贾疏:“牧人养牲,临祭前三月,授与充人繫养之。”姚孝遂先生说:牛“经过特殊饲养的就称之为‘牢’,未经过特殊饲养的仍称之为‘牛’。”[16]陈梦家先生说:“甲骨文字中有牢、 、
、 ,前两者是牲品,乃指一种豢养的牛羊。”[17]即“牢”是指专门圈养以供祭祀用的牲品牛。据此可知,“
,前两者是牲品,乃指一种豢养的牛羊。”[17]即“牢”是指专门圈养以供祭祀用的牲品牛。据此可知,“ ”就应该是指专门圈养以供祭祀用的牲品羊。关于“
”就应该是指专门圈养以供祭祀用的牲品羊。关于“ ”字,陈梦家先生说:“卜辞
”字,陈梦家先生说:“卜辞 疑是
疑是 字,《广雅·释宫》‘
字,《广雅·释宫》‘ ,庵也’,‘庵,廐,舍也’。”即陈先生说卜辞中的
,庵也’,‘庵,廐,舍也’。”即陈先生说卜辞中的 应是指廐舍,即养马之廐舍。目前,有四条卜辞中有“
应是指廐舍,即养马之廐舍。目前,有四条卜辞中有“ ”字,学者都认为其中没有一条是指祭祀之牲品的,都是指养马之廐舍。笔者认为其中一条第三期卜辞:“王畜马,在兹
”字,学者都认为其中没有一条是指祭祀之牲品的,都是指养马之廐舍。笔者认为其中一条第三期卜辞:“王畜马,在兹 ,母戊……王受又。”(《合集》29415)有可能是指用经过特殊饲养的马来作牲品。卜辞中有用马作牲品的记录(数量很少),但在殷墟却发现有用大量的马作牲品的遗迹[18]。准此,则第(3)版上的第一辞是于辛巳日卜问,问在未来第十天的辛卯日,用十头牛,并剖杀十头经过特殊饲养的牲品牛来祭祀先公河;用烧十头牛、并剖杀十头经过特殊饲养的牲品牛来祭祀先公王亥;用烧十头牛、并剖杀十头经过特殊饲养的牲品牛来祭祀先公上甲。第二条辞也是于辛巳日卜问的,问就在先公河的宗庙里同时祭祀先公王亥、上甲可以吗,“即”之意为就。则该版中的第一辞是卜问祭祀的内容,第二辞是卜问祭祀的场所。第(4)版的一条辞也是于辛巳日卜问的,辞残多字,但仍可看出是卜问在未来第十天的辛卯日燎祭先公王亥等的,辞意当与第(3)版的第一辞一致。第(5)版上有两条辞,两辞都是于辛巳日卜问的,第一辞问就在先公河的宗庙里同时祭祀先公王亥、上甲可以吗,辞意与第(3)版中的第二辞一致,只不过这里省略了“宗”字;第二辞残字较多,大概也是卜问就在先公河的宗庙里同时祭祀先公王亥的。以上(3)、(4)、(5)三版卜辞的内容基本相同,三版中的四条辞中都有王亥一称,四条辞中王亥的亥字都是从亥从隹,隹即鸟,即亥字作“
,母戊……王受又。”(《合集》29415)有可能是指用经过特殊饲养的马来作牲品。卜辞中有用马作牲品的记录(数量很少),但在殷墟却发现有用大量的马作牲品的遗迹[18]。准此,则第(3)版上的第一辞是于辛巳日卜问,问在未来第十天的辛卯日,用十头牛,并剖杀十头经过特殊饲养的牲品牛来祭祀先公河;用烧十头牛、并剖杀十头经过特殊饲养的牲品牛来祭祀先公王亥;用烧十头牛、并剖杀十头经过特殊饲养的牲品牛来祭祀先公上甲。第二条辞也是于辛巳日卜问的,问就在先公河的宗庙里同时祭祀先公王亥、上甲可以吗,“即”之意为就。则该版中的第一辞是卜问祭祀的内容,第二辞是卜问祭祀的场所。第(4)版的一条辞也是于辛巳日卜问的,辞残多字,但仍可看出是卜问在未来第十天的辛卯日燎祭先公王亥等的,辞意当与第(3)版的第一辞一致。第(5)版上有两条辞,两辞都是于辛巳日卜问的,第一辞问就在先公河的宗庙里同时祭祀先公王亥、上甲可以吗,辞意与第(3)版中的第二辞一致,只不过这里省略了“宗”字;第二辞残字较多,大概也是卜问就在先公河的宗庙里同时祭祀先公王亥的。以上(3)、(4)、(5)三版卜辞的内容基本相同,三版中的四条辞中都有王亥一称,四条辞中王亥的亥字都是从亥从隹,隹即鸟,即亥字作“ ”、
”、 、
、 形的鸟形状,可隶定作“
形的鸟形状,可隶定作“ ”。
”。
(6)□□[卜],贞:羗……[王]亥。(《合集》34295,《粹》51,三期。图1—7)
这是一版第三期龟腹甲刻辞。残字较多,仅存三个字,但大致可以知道是某日卜问以羌人祭祀先公王亥的。王亥之亥字,从亥从萑,作“ ”形,萑亦即隹,亦即鸟,字象有冠的鸟形,仍可隶定作“
”形,萑亦即隹,亦即鸟,字象有冠的鸟形,仍可隶定作“ ”。
”。
(7)四羊、四豕、五羌[于王]亥。(《合集》30448,《库》1064,三期。图1—8)

图1—7 祭祀王亥,亥字作鸟形
(《合集》34295)

图1—8 祭祀王亥,亥字作鸟形
(《合集》30448)

图1—9 祭祀王亥,亥字作鸟形
(《合集》22152)
这是一版第三期的牛胛骨刻辞,可能有残字。卜辞卜问用四只羊、四头豕、五个羌人来祭祀先公王亥。王亥之亥字,从亥从崔,崔亦即隹,亦即鸟,字作“ ”形,象有冠的鸟形,可隶定作“
”形,象有冠的鸟形,可隶定作“ ”。
”。
(8)又伐五羗[于]王亥。(《合集》22152,《京人》3047,三期。图1—9)
这是一版第三期龟腹甲刻辞。卜问“又伐”五个羌人来祭祀先公王亥。“又”读为侑,“伐”之义为砍头以杀,即杀伐之意,在甲骨文中多用作人祭的专名,即该辞是卜问杀伐五个羌人来祭祀王亥。王亥之亥字,从亥从崔,作“ ”形,象有冠的鸟形(该字下端残掉偏旁“亥”),其字可隶定作“崔”。
”形,象有冠的鸟形(该字下端残掉偏旁“亥”),其字可隶定作“崔”。
以上是迄今所见到的在王亥的“亥”字上加鸟形的全部卜辞,共是九条。其中第(1)版第一辞的亥字不但加鸟形,还在鸟形上加手形,会意为以手捉鸟。这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说“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的传说是相一致的。胡厚宣先生说:“王亥之亥而从鸟,乃商族以鸟为图腾之确证。”[19]这是十分正确的。
商人为什么要把鸟图腾的符号加在王亥的亥字上,而不是加在其他祖先的庙号上呢?胡厚宣先生说,这主要是因为王亥是上甲的父亲的缘故。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从王亥在商族的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上去寻找答案。
王亥是商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首先,典籍中王亥的名字多有所见就是证明。如: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
《楚辞·天问》说:“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清代学者徐文靖、刘梦鹏等都考定这句话中的“该”为人名,它与《史记·殷本纪》中的冥之子“振”、《世本》中的“核”、《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同一个人。[20]近代,王国维先生又根据商代甲骨文考证出古书中的“该”、“核”、“垓”、“振”就是卜辞中的王亥,也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竹书纪年》中的“子亥”,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但王氏又认为《史记》中的“振”,因与“核”、“垓”二字形近而讹[21],他的这一说法为后来的多数甲骨学者所信从。近年,李平心先生撰文不同意王国维的这个说法,他说:“振与核、垓二字并不相似,无由致误”,认为“振”在典籍中是有影踪可寻的。他考证《易·未济》的“震用伐鬼方”的“震”,就是《史记·殷本纪》中的“振”,证据是:“按着文法,这句爻辞与《既济》‘高宗伐鬼方’辞例相同,震用显然为人名。以史文比证,震当即《殷本纪》之振,也就是王亥;用即上甲微。”[22]对李平心先生的“震”是“振”是王亥的考证,笔者认为可以接受,这个考证使历来不得其解的“震用伐鬼方”的“震”字的意义,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过去将“震”训为威、训为惧是不可通的。但对他的“用”是指上甲微的说法,觉得还需要有更多的材料来给予证明才行。
其次,典籍中对王亥的事绩也略有记载,如: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王国维先生解释说:“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又说:“有易之人,乃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仇,故为之不宁也。”《山海经》、《竹书纪年》之“有易”,《天问》作“有扈”、“有狄”。王国维认为“扈,当为易字之误”,而“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23]
《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胲”是“亥”的通假字。
《吕氏春秋·勿躬篇》说“王冰作服牛”,王国维说:“案篆文冰作 ,与亥字相似,王
,与亥字相似,王 亦王亥之伪。”
亦王亥之伪。”
对于以上典籍中的“仆牛”、“朴牛”、“服牛”的意义,王国维先生说:“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24]这里,王国维是说王亥是发明驯服牛驾车的人。而胡厚宣先生则说:“服牛即仆牛朴牛,亦即牧牛”,“所谓‘牧夫牛羊’,即是放牧牛羊之意”,是说“王亥是发明牧牛的人”,“王亥是一个畜牧业的创始人。”[25]笔者认为,将王亥说成是商人畜牧业的创始人,这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不符。考古学的材料证明,人类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即考古学上的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了畜牧业;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畜牧业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氏族部落里,人们在经营农业的同时,饲养的家畜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地增多,其中牛、羊、鸡、犬、豕等的饲养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26]。商人社会最迟在其始祖契时就已经进入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因此,商人的畜牧业应该在契以前很久就已经产生了,说商人在契的六世孙王亥时才发明畜牧业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的。从“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牧夫牛羊”等的记载来看,应该说王亥是进一步促进了商人畜牧业的发展,而“胲作服牛”,又说明他发明了用牛驾车的技术。相土是契之孙,《世本·作篇》说:“相土作乘马”,是说相土时驯服马发明了用马驾车的技术。曹圉是契的四世孙(曾孙),有学者曾考释说:“曹即槽。《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杜预注云:‘养马曰圉’。《说文》圉字下云:‘一曰圉人,掌马者’。养马之人称圉,当是以牢圈养马而得名。则曹圉之名当与以槽牢从事牲畜的饲养有关。曹圉所处的时代为夏朝,说明商人在此时在畜牧业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础。”[27]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王亥是契的六世孙,相土的四世孙,曹圉之孙,他促进了商人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并驯服牛发明了用牛驾车的技术,这是继其祖先相土发明用马驾车的技术之后的又一重要发明,有学者还分析说,王亥是中国商业第一人,是中国商业的鼻祖,因为王亥时期商氏族的畜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亥就从事氏族间的商业贸易活动,他最后一次贸易活动就是与有易氏的交易,由于引起有易氏的不满,被有易之君緜臣所杀,王亥的商业贸易活动使商氏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28]。因此,在商人的眼里,王亥是个有大功德的祖先,再加上他是“能帅契者”的上甲微的父亲[29],所以受到后世子孙的尊重,称其为高祖[如前举的第(1)版卜辞],受到隆重的祭祀。并且在祭祀时,在其名字“亥”字上加上远古商氏族的鸟图腾的符号,这说明在商人的眼里,王亥是商部族的伟人和英雄。商人给予王亥隆重的祭祀,由下面几条祭祀卜辞即可见一斑[30]:
(9)四羊、四豕、五羌[于王]亥。(《合集》30448,《库》1064,三期)
(10)又伐五羗[于]王亥。(《合集》22152,《京人》3047,三期)
这两版卜辞前文已例举过[见第(7)、第(8)辞],前已指出该两辞中王亥的“亥”字上都加鸟形。这两辞都是卜问用五个羌人来祭祀王亥的,即对王亥进行人祭。这说明商人对王亥给予厚重的祭祀。

图1—10 祭祀王亥
(《合集》14724)
(11)贞:酒王亥。
二羊、二豕、五十牛于王亥。
来辛亥燎于王亥三十牛。
 于王亥。
于王亥。
翌辛亥 于王亥四十牛。(《补编》100正,一期)
于王亥四十牛。(《补编》100正,一期)
该版卜辞卜问用二羊、二豕和五十牛、或用四十牛、或用三十牛来祭祀王亥,用牲数量之多说明对王亥给予厚重的祭祀。
(12)贞: 于王亥,
于王亥, 三白牛。(《合集》14724,一期。图1—10)
三白牛。(《合集》14724,一期。图1—10)
该辞卜问用三头白牛祭祀王亥。《礼记·檀弓上》说:“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该辞卜问特用白牛祭祀王亥,说明商人对王亥是非常重视和非常尊崇的。所以,后世商人要将鸟图腾的符号加在高祖王亥的亥字上。

图1—11 祭祀鸟
(《合集》14360+《英藏》1225,即《缀合集》168)
远古时期的商氏族以玄鸟为图腾,人们崇拜鸟,对鸟怀有敬畏之情。吕大吉先生说:“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物既被氏族社会奉为图腾,就会自然而然地在心中产生某种敬畏之情。”[31]事实确实如此。商人社会由始祖契发展到武丁时期,已经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四代,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在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找到后世商人对鸟怀有崇拜和敬畏的材料。下面两版卜辞就证明武丁时期的商人仍然崇敬着鸟,他们对鸟进行祭祀:
(13)贞:方帝。七月。
贞:帝鸟一羊、一豕、一犬。
贞:帝鸟三羊、三豕、三犬。
丁巳卜,贞:帝鸟。(《合集》14360+《英藏》1225[32],一期。图1—11)
该版卜辞中的“帝”是祭名,是为“禘”祭。何为禘祭?自汉代以来有三种说法:一曰是时祭,即四时之祭;二曰殷祭,即大祭;三曰郊天之祭,即郊祭昊天。近见严一萍、王辉二先生的论证,与商代的事实比较接近。严先生说:“按帝 与燎
与燎 柴
柴 为一系,柴为束薪焚于示前,燎为交互植薪而焚,帝者以架插薪而祭天也。三者不同处,仅在积薪之方式与范围。故辞言‘帝一犬’,犹他辞之言‘燎一牛’也。”[33]王辉先生在全面归纳、研究了卜辞中的帝字的字形以后,认为:“我们可以把帝字看作是由头上的一和下部的
为一系,柴为束薪焚于示前,燎为交互植薪而焚,帝者以架插薪而祭天也。三者不同处,仅在积薪之方式与范围。故辞言‘帝一犬’,犹他辞之言‘燎一牛’也。”[33]王辉先生在全面归纳、研究了卜辞中的帝字的字形以后,认为:“我们可以把帝字看作是由头上的一和下部的 (或
(或 )二部分所组成……
)二部分所组成…… 祭是柴祭,
祭是柴祭, 乃是束祭,也是柴祭的一种,所以从字形上看,禘必然是火祭的一种。问题是帝字上部的一究竟代表什么?一在甲文中可以代表各种意义,但在帝字顶部,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指示符号,代表天空……帝字从一从
乃是束祭,也是柴祭的一种,所以从字形上看,禘必然是火祭的一种。问题是帝字上部的一究竟代表什么?一在甲文中可以代表各种意义,但在帝字顶部,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指示符号,代表天空……帝字从一从 (或
(或 ),
), 或
或 表示柴祭,一指明祭祀的对象为居于天空的自然神。”[34]二位先生所论有得有失。笔者接受他们关于禘祭是火烧柴薪之祭的考证,但不接受他们关于禘祭是祭天和只是祭居于天空的自然神的说法。因为殷墟甲骨卜辞表明,商人是不祭祀天的;而且,禘祭也不只是祭祀居于天空的自然神,而是还用来祭祀其他自然神。上举第(13)版卜辞就是卜问禘祭鸟的,该辞的鸟字作
表示柴祭,一指明祭祀的对象为居于天空的自然神。”[34]二位先生所论有得有失。笔者接受他们关于禘祭是火烧柴薪之祭的考证,但不接受他们关于禘祭是祭天和只是祭居于天空的自然神的说法。因为殷墟甲骨卜辞表明,商人是不祭祀天的;而且,禘祭也不只是祭祀居于天空的自然神,而是还用来祭祀其他自然神。上举第(13)版卜辞就是卜问禘祭鸟的,该辞的鸟字作 形,对该字,王襄先生释为雉[35],胡厚宣先生说:“鸟和隹为一字,从一者象矢形”,并引《说文》等古书证明“雉为一种美丽的鸟名。”[36]准此,则第(13)版卜辞是卜问用一羊、一豕、一犬还是用三羊、三豕、三犬来禘祭鸟。由禘祭是用火烧柴薪进行祭祀来看,鸟在天上飞,用火焚烧祭品使烟雾升天,才能使鸟享受到祭品。
形,对该字,王襄先生释为雉[35],胡厚宣先生说:“鸟和隹为一字,从一者象矢形”,并引《说文》等古书证明“雉为一种美丽的鸟名。”[36]准此,则第(13)版卜辞是卜问用一羊、一豕、一犬还是用三羊、三豕、三犬来禘祭鸟。由禘祭是用火烧柴薪进行祭祀来看,鸟在天上飞,用火焚烧祭品使烟雾升天,才能使鸟享受到祭品。
(14)庚申卜,扶:令小臣取祊羊鸟。(《合集》20354,一期)
这是一版 组卜辞。由贞人扶在庚申日卜问,问命令名叫取的小臣去祊祭“羊鸟”可以吗。祊,有人释为丁,祊在该辞中是祭名。对“羊鸟”之义,胡厚宣先生说:“羊或读作祥。祥鸟犹《史记·殷本纪》‘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之祥雉。”[37]其说有理。该辞的鸟字作“
组卜辞。由贞人扶在庚申日卜问,问命令名叫取的小臣去祊祭“羊鸟”可以吗。祊,有人释为丁,祊在该辞中是祭名。对“羊鸟”之义,胡厚宣先生说:“羊或读作祥。祥鸟犹《史记·殷本纪》‘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之祥雉。”[37]其说有理。该辞的鸟字作“ ”形。以上两版卜辞证明在殷商时期,人们仍然像远古时期一样对鸟怀有崇拜的心理[38]。这种残余信仰的存在,也证明了远古时期的商氏族是以鸟为图腾的。
”形。以上两版卜辞证明在殷商时期,人们仍然像远古时期一样对鸟怀有崇拜的心理[38]。这种残余信仰的存在,也证明了远古时期的商氏族是以鸟为图腾的。
殷商时期的人们对鸟还有畏惧心理,下面三版卜辞可以证明:
(15)庚申卜, 贞:王勿……。之日夕
贞:王勿……。之日夕 鸣鸟。(《合集》17366正反,一期)
鸣鸟。(《合集》17366正反,一期)
(16)丁巳[卜],贞:……鸣……祸。(《合集》17367,一期)
(17)□□[卜],贞:……鸣……祟。十一月。(《合集》17368,一期)
第(15)辞由贞人 在庚申日卜问,问商王在当天不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会不吉利,验辞记录在“之日夕”即庚申日当天夜间有鸟鸣发生。该辞的鸟字亦作“
在庚申日卜问,问商王在当天不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会不吉利,验辞记录在“之日夕”即庚申日当天夜间有鸟鸣发生。该辞的鸟字亦作“ ”形。由此可以看出在商人的心里,认为鸟鸣是不吉利的,做什么事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第(16)辞于丁巳日卜问,辞虽残,但由保留的“鸣”、“祸”二字来看,应该是说鸟鸣会带来祸患。第(17)辞残掉多字,但由残存的“鸣”、“祟”二字来看,应该也是说鸟鸣会带来祸祟的。商人这种惧怕鸟的心理,在古文献中也能找到其痕迹,如《史记·殷本纪》记载说:“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这是记录商王武丁在祭祀成汤的时候,大白天的,突然有飞鸟落在鼎耳上鸣叫,武丁很害怕。以上卜辞和古书的记载说明,即使到了殷商时期,人们还保留着对鸟的崇敬和畏惧的心理。这种对鸟的残余信仰的存在,说明在远古的时期,商人确实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
”形。由此可以看出在商人的心里,认为鸟鸣是不吉利的,做什么事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第(16)辞于丁巳日卜问,辞虽残,但由保留的“鸣”、“祸”二字来看,应该是说鸟鸣会带来祸患。第(17)辞残掉多字,但由残存的“鸣”、“祟”二字来看,应该也是说鸟鸣会带来祸祟的。商人这种惧怕鸟的心理,在古文献中也能找到其痕迹,如《史记·殷本纪》记载说:“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这是记录商王武丁在祭祀成汤的时候,大白天的,突然有飞鸟落在鼎耳上鸣叫,武丁很害怕。以上卜辞和古书的记载说明,即使到了殷商时期,人们还保留着对鸟的崇敬和畏惧的心理。这种对鸟的残余信仰的存在,说明在远古的时期,商人确实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
那么,商人崇拜的是什么鸟呢?也即商人是以什么鸟为图腾的呢?前文列出的古文献材料记录说远古时期的商始祖是由简狄吞玄鸟卵所生,也即商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那么“玄鸟”又是指的什么鸟呢?自古以来,人们对“玄鸟”的所指有几种说法:
1.对《诗经·商颂·玄鸟》中的“玄鸟”,战国时期的屈原在《天问》中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39];在《九章·思美人》中说:“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在《离骚》中又说:“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这里说的玄鸟是指凤凰[40]。现从此说者有胡厚宣先生[41]。
2.《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诱注:“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王逸注《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说:“简狄,帝喾之妃也。玄鸟,燕也,贻,遗也。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坠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王逸注《九章·思美人》之“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说:“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又郑玄笺《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玄鸟, 也。”又说:“玄鸟,燕也。一名
也。”又说:“玄鸟,燕也。一名 。”又在前引第二条材料中郑玄注《诗·商颂·长发》也说玄鸟是指
。”又在前引第二条材料中郑玄注《诗·商颂·长发》也说玄鸟是指 ,也即燕子。许慎《说文解字》“燕”字条说:“燕,玄鸟也。”以上是说《吕氏春秋》和汉代人的笺注中都说玄鸟是指燕子。目前学者多从此说。
,也即燕子。许慎《说文解字》“燕”字条说:“燕,玄鸟也。”以上是说《吕氏春秋》和汉代人的笺注中都说玄鸟是指燕子。目前学者多从此说。
3.近年又有人提出“玄鸟”是指鸱 ,即猫头鹰,说商人是以鸱
,即猫头鹰,说商人是以鸱 即猫头鹰为图腾的[42]。
即猫头鹰为图腾的[42]。
总之,迄今对“玄鸟”的所指有凤凰、燕子、鸱 (猫头鹰)三种说法。那么,“玄鸟”到底指的是哪一种鸟呢?“玄鸟”之“玄”,《说文》谓是“黑而有赤色者为玄”。燕子的颜色与“黑而有赤色”不太相近;并且燕子的“燕”字,甲骨文作“
(猫头鹰)三种说法。那么,“玄鸟”到底指的是哪一种鸟呢?“玄鸟”之“玄”,《说文》谓是“黑而有赤色者为玄”。燕子的颜色与“黑而有赤色”不太相近;并且燕子的“燕”字,甲骨文作“ ”、“
”、“ ”、“
”、“ ”等形,其特征是“翅膀尖而长,尾巴分开象剪刀”[43],它们与前举的加在商人高祖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大不相同,并且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有的带有凤冠(带凤冠者应是雄性,不带凤冠者应是雌性),而燕子是没有凤冠的,所以玄鸟不是指燕子;如果远古时期的商氏族是以燕子为图腾的,那么甲骨文中加在王亥的“亥”字上的图形应该是上举的燕子形而不应是现在的鸟形。甲骨卜辞中的凤字多借为风,其写法作“
”等形,其特征是“翅膀尖而长,尾巴分开象剪刀”[43],它们与前举的加在商人高祖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大不相同,并且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有的带有凤冠(带凤冠者应是雄性,不带凤冠者应是雌性),而燕子是没有凤冠的,所以玄鸟不是指燕子;如果远古时期的商氏族是以燕子为图腾的,那么甲骨文中加在王亥的“亥”字上的图形应该是上举的燕子形而不应是现在的鸟形。甲骨卜辞中的凤字多借为风,其写法作“ ”、“
”、“ ”等形,这种写法与加在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也不相类,凤字虽然有凤冠,但与加在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凤冠相比,却另有特色,并且凤冠也要高得多,而且其尾部是长大而飘逸的;同时凤凰又不是“黑而有赤色”的,所以玄鸟也不应是指凤凰;又在前引的《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的一段话中,凤鸟与玄鸟是并列的,这也反映出玄鸟不是指凤鸟也即不是指凤凰。至于猫头鹰,则是“身体淡褐色,多黑斑”[44]的,它的颜色与“玄”所指的颜色不同;它的长相与甲骨文中加在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也相去甚远,因此,玄鸟更不是指猫头鹰。甲骨学者刘源先生曾就孙新周所说甲骨文中的“萑”、“雚”是猫头鹰的象形,商人的祖先图腾是猫头鹰一说,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给予了否定[45]。总之,玄鸟不是指猫头鹰是无可质疑的。
”等形,这种写法与加在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也不相类,凤字虽然有凤冠,但与加在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凤冠相比,却另有特色,并且凤冠也要高得多,而且其尾部是长大而飘逸的;同时凤凰又不是“黑而有赤色”的,所以玄鸟也不应是指凤凰;又在前引的《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的一段话中,凤鸟与玄鸟是并列的,这也反映出玄鸟不是指凤鸟也即不是指凤凰。至于猫头鹰,则是“身体淡褐色,多黑斑”[44]的,它的颜色与“玄”所指的颜色不同;它的长相与甲骨文中加在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也相去甚远,因此,玄鸟更不是指猫头鹰。甲骨学者刘源先生曾就孙新周所说甲骨文中的“萑”、“雚”是猫头鹰的象形,商人的祖先图腾是猫头鹰一说,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给予了否定[45]。总之,玄鸟不是指猫头鹰是无可质疑的。
笔者根据《说文》对“玄”字的解释和甲骨文中加在王亥的“亥”字上的鸟形推断,认为“玄鸟”应是指“黑而有赤色”的、短尾的、雄性头上有凤冠的鸟类(屈原和《吕氏春秋》及汉代人都各说出了它的部分特征)。至于这种特征的鸟到底是什么鸟,则还有待于将来请教于鸟类学家了。
前已说明,在原始氏族社会中,“人类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不仅不可能把与自己生存攸关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作为支配的对象,而且反把它们当作支配自己生存和生活的神秘力量。这两种力量就在原始人的观念中表现为对超自然的自然力量和对超人间的氏族祖先的崇拜,这两种宗教观念是原始宗教的基本观念,由此观念而象征化为两种基本的崇拜对象。”[46]换句话说,这两种基本的崇拜对象就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而图腾崇拜正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一种最古老的宗教崇拜形式。远古时期的商氏族就是把对自然物玄鸟的崇拜与对其祖先的崇拜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他们的图腾崇拜。商氏族的玄鸟图腾崇拜符合吕大吉先生提出的关于宗教的四要素:即宗教的观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宗教的行为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因此,图腾崇拜是商人宗教的起源。我们由距商始祖契二十三代的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推测,远古时期的商氏族所崇拜的自然物应该也是比较多的。(详见后文)
殷墟甲骨卜辞和商代金文透露出远古时期的商氏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此外,有学者还提出探寻古人图腾崇拜的另一条途径,即:“古人姓名和古代族名,也是可供考察我国古代图腾崇拜的一种依据。”并指出在“殷墟卜辞里,把殷人周围的民族称为‘马方’、‘羊方’、‘虎方’、‘林方’等。这种族名,可能来源于他们所崇拜的图腾对象——马、羊、虎、林等动植物的名称。”[47]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殷商时期这些部族的名称也或许就透露出了这些部族在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情况。另外,在我国的古籍中,还记录有大量的图腾氏族的名称,这里就不烦一一备举了。
殷墟甲骨卜辞和商代金文表明,即使到了商始祖契的二十三世孙武丁时,商人宗教所崇拜的对象仍然是诸多自然神和各世祖先神。其中对自然神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但对祖先神的崇拜却是贯穿于整个商王朝的。
[1] 以下所述关于宗教起源的资料皆引自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各派宗教起源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3]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62页。
[4]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页。
[5] 转引自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
[6] 见《中国民族志参考资料汇编》,下编,第55页。这里转引自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
[7]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8] 见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9] 胡厚宣先生注曰:“嘉原作喜。王逸洪兴祖朱熹注具云喜一作嘉。《汉书·礼乐志》《续汉书·礼仪志》引此具作嘉。按当以作嘉为是。顾炎武《唐韵正》说:‘今本嘉作喜,是后人不通古音而妄改之也。’”(见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11] 同上。
[12] 刊《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以下所引于先生之说皆出自此文,不再另作注明。
[13]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14] 笔者一直怀疑卜辞中有些“酒”字不是指通常的酒,而是指祭祀之意。详待另研。
[15] 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9片考释,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6] 见《牢、 考辨》,《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考辨》,《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17]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6页。
[18] 见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01页。
[19]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20] 李平心:《王亥即伐鬼方之震》,见《李平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
[22] 李平心:《王亥即伐鬼方之震》,见《李平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3]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
[24]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
[25]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26] 见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第三章、第四章,中华书局1984年版。
[27] 见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28] 王瑞平:《王亥与中国商业贸易的肇端》,《光明日报》2004年6月1日《理论周刊》版。
[29] 《国语·鲁语上》:“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
[30] 商人对王亥祭祀的详细情况,请见第四章第一节。
[31]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32] 该版卜辞为蔡哲茂先生缀合。见《甲骨缀合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版,第168片。
[33] 严一萍:《美国纳尔森艺术馆藏甲骨卜辞考释》,艺文印书馆1973年版,第8页。
[34] 王辉:《殷人火祭说》,《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版。
[35] 王襄:《簠室殷契类纂》,卷四,1920年版,第18页。
[36]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37] 同上。
[38] 胡厚宣先生曾引《乙编》的三版卜辞,即今《合集》11497正反、《合集》11498正反、《合集》11500正,来证明商人还祭祀鸟星。实误。今已证明卜辞中的“鸟星”不是指星,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6页。
[39] 嘉原作喜。喜是嘉之误。见前第5页注③。
[40] 郭沫若说:“‘凤凰既受诒’,以上下文案之,实即玄鸟传说。《天问》篇,‘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九章·思美人》,‘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玄鸟致诒即凤凰受诒,受授省,诒贻通,知古代传说中之玄鸟实是凤凰也。《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注家以玄鸟为燕,乃后来之转变。”见《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12页。此处转引自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王泗原亦说:“凤凰受诒与《天问·思美人》的玄鸟致诒是一回事……这玄鸟即凤凰。”见《楚辞校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41] 胡厚宣先生在1964年发表的《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一文中从屈原之说,认为“玄鸟”是指凤凰,并用甲骨文中祭祀“帝史凤”的卜辞来做证明。但在1977年发表的《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一文中就只说屈原“把玄鸟说成凤凰”,而没有发表个人的意见。
[42] 孙新周:《鸱 崇拜与华夏历史文化之谜(中)》,《北京晚报》2002年11月9日第34版“五色土副刊”。
崇拜与华夏历史文化之谜(中)》,《北京晚报》2002年11月9日第34版“五色土副刊”。
[43]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53页。
[44] 同上书,第854页。
[45] 刘源:《也谈甲骨文中的“萑”、“雚”》,《北京晚报》2002年12月2日第36版“五色土副刊”。
[46]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引文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47]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