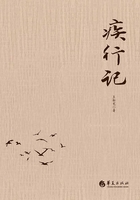
火村工作队
1976年,谁都希望但都预料不到,这一年成了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终点。
这一年,市民政局党委在全系统组织开展基本路线教育,为了体现对知青工作的重视,把所属的火村果园农场,作为开展路线教育的重点单位。同时,出于培养青年骨干的考虑,从下属事业单位、福利厂选调了一批人,由局政治部主任徐源本带队,组成了工作队进驻农场,从当年9月到翌年2月,历时半年之久。
火村果园场,在广州市远郊萝岗镇的辖区内,交通虽然有火车、长途公共汽车,但车站离农场都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出行并不方便。但地理位置离广州市区近,总算是个不错的知青安置点。因此,除了正常毕业生分配渠道来的,还有带照顾的成分的,比如来自民政系统、省直机关的干部子女等。
农场设有场部,下有基建队、大田队、种植队、养殖队、小工厂等。我和来自民政局所属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另两位同志,合成一个小组派到小工厂,当时也称“五队”。住宿则和分在“三队”的工作组同志一起。
那时候,不能说我做思想工作没有一点经验,但是做知青的工作,相比做学生、青年工人的工作,完全是两码事。对当时情景有下面的记载:
“我觉得,要改变知青队的面貌,就要做好后进知青的转化工作。但一开始和个别比较后进的青年接触,就碰了钉子。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不吭声,再三问也不开口,反倒听到讥笑、讽刺的声音;开会要求遵守会场秩序,他们不听。耐下心来和他们交谈,除听到粗言烂语外,没有几句正经话。有的还声言不和工作队讲道理,认为工作队是来整他们的,戒心很重。”可见,“文革”的“造反有理”“读书无用”和“怀疑一切”,对青年的荼毒有多深。
虽然腿不方便,但与农场知青的“三同”我坚持了下来。除了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外,每到假日回广州,我就去家访,与家长一起做思想教育工作。
有一次,要找一位青年谈心沟通情况,我和另一位同志白天两次到家里,都找不到人,只好晚上再去,等到11时多,才见上面。此情此景触动了这位年青人,他敞开了心扉,一直谈到深夜12点多,向我们反映了很多具体情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继续帮助他,后来他的变化很大,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成了队里的骨干。
还有一次,我费了老劲找到家住得很偏僻的一个知青家里,他又惊讶又感动地说:“怎么都想不到你会来我家,工作队同志这么关心,我一定改正错误,争取做好。”小伙子真没有食言,在后来的表现中有了明显的转变。
由于五队和三队离得很近,两个队是合用一个大厨房。我看到厨房的鼓风设备年久失修,就和队友一起对其做了更新改造,减轻了厨房知青的劳动强度。当时伙食条件差,每天都是糙米加青菜,每顿3~4两米饭,隔天有3分钱猪肉,也就是每周只有1角钱肉食。肚里没油水,白天干活累啊,有的年轻人熬不住了。
一天深夜2点左右,突然有人把我推醒:“嘿,王同志,吃烤雀仔吗?”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眼前晃了一下,我迷迷糊糊摇摇头,又睡了。第二天,我走到一间知青宿舍,感觉怎么有点怪怪的,再仔细看,床全都变矮了!在我的追问下弄明白了,原来他们白天抓了几只小鸟,等天黑后偷偷开荤解馋。他们不敢到厨房去,没火怎么办呢?索性“就地取柴”,他们把自己宿舍里的床腿锯了下来,“野外烧烤”就成了。
我暗暗侥幸:好家伙,幸亏没吃!否则我这工作队同志也“下水”了。
我们到农场的时候,知青新宿舍已经落成有一阵子了,但屋里的窗框一直没装上玻璃。岭南冬天气候是湿冷湿冷的,特别在城外没有建筑物的阻挡,北风呼呼刺骨难熬,连壮实的男青年都扛不住,女知青更是叫苦不迭。我见此情景,主动去找领队的大老李商量:我们设法把玻璃装上吧,这件事是早应该做的。李景华组长很快与场部协调,解决了窗户玻璃来源,紧接着带领小组同志,几天时间就把玻璃全装上了。从这件事开始,队里知青对我们的“戒心”开始化解了。
最初,我召集五队的知青开会,屋子里没几张像样凳子,人都靠着墙根蹲着、挤在门口站着,实在不像开会的样子,他们以前都是这样。这状况不行啊,我脑子一转,先做了个坦诚的检讨:“工作队召集开会,却没有凳子给大家坐,是我们没准备好!”以后我们在屋里增加了凳子,人坐整齐了就有开会的气氛,“正常秩序”在无形中被大家慢慢接受了。
阿强和阿鸣,他们俩在队里最不服从“管束”,是让知青队长挺头痛的“人物”。阿强的家庭条件较困难,阿鸣则是干部子弟,这点从他们平时的衣着就能看出来。我在晚上经常到知青宿舍聊天,借此指出他们的毛病,哪怕看到一点点小进步,也及时在场面上表扬。当寒冷天气要来时,我注意到阿强的衣服很单薄,借回厂办事的机会,我托人弄了一张计划内的棉衣票,当时候可稀罕哪,给一个厂统配下来的也没几张啊。凭它我到高第街商店买了一件大号蓝色棉衣。当把新棉衣送到阿强手里时,他愣住了,用手在眼角拭了一下,低着头久久不语。
1976年3月5日,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那几天,父母的心情似南方的雨天阴沉沉的,父亲下班回来就坐在客厅,不停地抽烟,话也少了。几天后,我们单位已经准备好了开追悼会,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说不开了,也没有任何解释。怎么办呢?我和两个要好的伙伴不约而同想到了一块,在朋友家里自设了灵堂,我们默默无语肃立着,一起遥祭敬爱的总理。接着,也就半年时间里,朱老总、毛主席竟先后离去,巨大的悲痛阵阵袭来,大家有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10月初的一个晚上,两个组的同志在宿舍床上盘腿坐着聊天,我摆弄着一部巴掌大的微型收音机,突然,从微弱的信号中断断续续传出“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久违的歌声让大家惊喜不已,真有绵绵阴雨中突然见到一缕阳光的感觉,苏丽英情不自禁跟着唱了起来,我们赶紧摆手示意她小声点啊,这歌是上面不让唱的。
“四人帮”倒台了!我们和五队知青一起,兴高采烈地集合游行,从宿舍一直走到农场场部前,其他队也先后到了,我见到人们有种难以言语的轻松,欢笑声一片,热闹如同隔三岔五的农村赶集日。
1977年元旦后,工作队的任务基本完成了。毕竟费了不少心力,我没有完全放下心来,回城后又给曾经“帮教”过的知青写信,再三叮嘱他们要遵守农场纪律,安心劳动锻炼。2月间,我意想不到收到一封回信,下面是信的原样内容:
王同志你好
接到一信,我们心甚喜多得你的心情指教,关心教育,我,不少叫我做好工作,不正当事切勿做,但经过你教育后,我尽力学习,感谢你多的通讯帮助,但我文化太小写信不好请为原谅,如有空时间请到来舍下多的教育为要此致。
祝你身体健康
春节俞快
1977年2月11日晚11时25分提
强.鸣合
我看了信以后,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欣慰和感动。阿强、阿鸣这些小青年,放到现在看就是“调皮”“任性”,他们的心地是朴素、善良的,当时他们的表现,多是出于对希望和前途迷茫而“放任、发泄”而已。
我随后又写信,向五队知青干部了解近来的情况,也很快收到了回信,信里面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特别在‘困难的时候’,尤其受到鼓舞。目前,队里的工作刚转入正轨,由于电木粉到今还没有,所以,原压塑车间的人力全部投入包装车间,除少数人开机器,大多数都是订盒的。人员、生产到目前为止才叫稳定下来,至于队里的其他方面工作,今后还要逐步来的。相信五队的形势一定会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的,请工作队同志等着好消息吧。”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难忘、很有意义的经历。在1977年3月召开的民政工业公司学大庆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会上,我讲了这样一段体会:
“在做工作过程中,自己自始至终注意坚持既做教育者,又做受教育者,处处注意学习知青的长处;重调查,对后进青年做认真研究,不凭主观想象;对有反复的青年不急躁斥责,而是耐心分析原因,更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后进知青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使队的革命和生产局面有了一些改观,自己从中也受到深刻教育,有了新的提高。通过三个月的锻炼,自己深感到这次确是为自己补了在工厂里难以补上的一课,使自己在改造思想上又有了新的收获。”
唯独使大家很难过的,是与我们一起参加工作队的广州档圈厂政工干部苏丽英,她是从海南回城的老知青,工作泼辣能干,是个很优秀的女同志。她不幸在1981年患癌症去世了,留下了不到3岁的小女儿。我们一起去知青三队、五队工作的同事,每当说起阿苏,都痛心惋惜不已。
思之得
无论是机关还是基层,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体现在善于做“思想”活,缘由是你工作面对的是“活人”而不仅是“物件”。善于沟通思想的人,一般来说,合作系数、包容系数都比较高,在群众中容易站住脚,这比什么都重要。
让被领导者真的心悦诚服,你才可能将“承诺”付诸实现。领导者把话说得再好,不能开花结果,那就形同大街上的“标语口号”,时间长了,剩下的可能就是反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