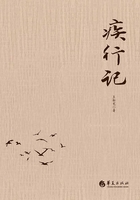
民政福利厂,她的历史贡献
对“福利生产单位”的起源,曾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秘书长的“老民政”林泰有过这样的回忆:“福利生产这项工作起源于1958年‘大跃进’,全国街道组织所有的闲散人员(包括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创办‘街道生产’。民政部门也办了许多工厂。”“当时民政部门组织的生产有几种类型:一是生产救济型,主要吸收社会困难户参加的工厂;二是助残型,主要吸收残疾人参加的工厂;三是优抚型,主要吸收烈军属参加的工厂;四是服务型,主要是为福利事业服务的工厂,如假肢工厂、助听器厂、火葬机制造厂、残疾人专用设备制造厂等。”
要更微观地了解福利厂的历史,可以从我们的厂子说起,它自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1958年创建的“社会福利五金制品厂”到后来的“电器五金制造厂”,再到1966年更名后的“东升电器厂”“电焊机厂”,它走过了近60年艰苦创业、奋斗发展的历史。它虽然是一个小厂,却是原生态社会里无数细胞之一,当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就成了观察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轨迹中一个真实的窗口。
它诞生于“大跃进”的年代,那时候并没有“福利企业”的概念。它的出发点是以安置城市贫民、烈军属荣复转退军人和残疾人为主,还有经改造从良的妇女、解除劳教人员,甚至在“反右”中提前从部队、公安队伍“退役”的人员,等等,体现了当时“教育人、改造人”和“给出路”的政策精神。广州市的这类单位从1958年成立起至1966年年初,上级管理部门是民政局生产教养科,直到民政工业公司成立后的1966年1月,才结束被“生产教养”的历史。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福利工厂是由民政局的“劳动教养”部门管理的,可能是源于特殊的联系或交叉,因为“劳动”与“教养”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特别要说的是“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的形式,这是党和政府解决当时困难的创举,体现了新生政权为人民的本色,在安置残疾人(当时称残废人)就业方面起了主渠道作用,使残疾人在劳动保障和社会发展中享受到他们的基本权利,这是盘古开天地的第一回,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收拾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的本事。
作为南方最大城市的福利企业,它曾经拥有自己独特的卓越和光彩:在全市各类福利企业中,它长期经营状况良好,在系统内上缴利润最多;它拥有完整的技术装备,专业化生产水平比较高,同类产品的规格、型号齐全;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培养出来的企业骨干多;残疾员工安置比例高,培养出了最早一批残疾人骨干;作为公司系统企业全面整顿的样板,为全国福利企业改革提供了经验。
所谓盛极而衰,衰竭而亡,是无数福利工厂现实中的写照。如果说主客观原因,的确难分孰重孰轻,主观认识是来自当时历史条件的反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苛求前人。比如,市民政局每年开总结会,领导的工作报告一贯是把福利企业放到最后讲,是因为文章体例还是重要性排列,这我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没列入民政工作的核心业务。
从根本上说,问题的症结在于:一是体制上结构性矛盾,工厂长期实行“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事业性质成了单位的胎记,民政企业把它看作一件“破棉袄”,可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以当时的大环境和自身状况,要企业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成了难以逾越的悖论;二是当时的生产单位属计划经济的产物,习惯了二三十年“统购包销”的日子,企业内外都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其他强势行业无奈之下也纷纷“关停并转”,福利企业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到“文革”后期,曾热闹了一番的“民字不出头,工业闹归口”,实际上有它的合理性。当时能归口的,就是比较起来条件最好的,否则人家系统也不愿要。问题就在这里,把“好单位”放走,哪个领导愿意被人称作“李鸿章”呢?还有人站在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认为是部分的厂领导干部想离开民政,当时有“出生入死”一说,意思是离开民政部门的干部发展得快些,他们有机会安排到更有“前景”的岗位,亦同样能担当重任,这样的例子的确也能举出一些。最后,像电器厂、电器元件厂等有条件的厂也没有归口到机电行业。如此一来,客观上失去了行业保护、技术联盟、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乃至干部交换流动等方面的机遇,也成为后来走向颓势的潜在因素。
如同物质不灭原理昭示的,“天无绝人之路”,经过凤凰涅槃,在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托举下,借助国家长期坚持的减免税等政策,一些老福利企业枯木逢春,以它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了下来,而大批新型的福利企业则脱颖而出,成为解决困难群体就业的主要平台,它们是当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思之得
从救济型的生产单位到福利工厂,可能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制度安排。历史没有假设一说,辩证地看待过去,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客观性,对待过去,要理性地走进去,清醒地走出来。现实是将来的历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厘清立足的历史方位,规划未来的“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