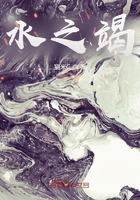
第175章 张良(1)
近些时日,我常忆起从前。
授衣之际,霜降满地。叔旦宅邸的院落中,秋意渐染,草木枯谢,唯独那人赠的木槿还是开着的。淡粉色的花瓣逐片绽开,不似桃花般香得浓郁,却是重重叠叠,数月不衰,别有一番韵味。
入冬后,那人又送来一株山茶。屋檐上的白雪落到花上,将那雪捧在手心里,从中散发出雅淡的香气,至今让人回味。
叔旦从来不许我在那人的花旁练剑,说是万一我不小心伤了花枝,那人得知后必定生气。回想起来,我其实从未见过那人。我见过的只有他种的花,以及那一日番君施行魂印之术时,浮现而出的他的灵魂。
传言燕召公性情恬静,写了一手好书法,无人能及。现观四象令牌上浮现而出的刻字,确是隽秀有力,笔锋老道。除了沉稳之外,还隐含着一股不易察觉的狂放不羁,似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十分不符。
低调地种着花,低调地安抚民心,低调地在封印前将自己一部分魂魄刻入四象之中,以文字启示后人,与天力抗衡。
所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朱雀上的「浴火重生」,是为番君,也是为他自己,刻下的最后一句话。
只是那人重生于令牌之中,却不知番君会重生在哪里?万千为此而亡的人,又要如何寄托?我又能,承载得了多少呢?
朱雀魂印缔结,继而骤雨倾盆。中原脱离了十数年之久的干旱之苦,关中亦不再有我的容身之处。
万物复苏之际,再惹事态非明智之举。白虎不知去向,我只得将其余三象的封印暂且搁置,偕同仲云一起,带番君的遗体回长沙。趁着夜色,将他与他的夫人合葬于一处。
昔年长沙王府变故之时,百姓为他夫妇二人修建的祠堂至今犹在,只是破落了几分,原本拔净的杂草长至没膝。虽然继任的长沙王禁止无关的平民靠近王冢,但仍可见到坟前隔三差五被放上些花果,有时还会点上一炷香,不知是何人所为。
史书记载不下的,却悄悄种在了人们心底。河上公最推崇的那位圣贤曾说过一句「谷神不死」,我至今才算真正明了。
暂居于长沙边郊客栈,那是除了偶尔有旅人路过求碗酒水,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店,连店主都时常不见人影。品着农家自酿的果酒,仲云问我之后的打算。我说出一个地名后,他显得有些讶异。
“要去晋阳吗?我本以为,你会照那小皇帝所说前往齐国。虽然我们没有拿到皇帝的手书,但若是好好说明情况,齐王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我摇头不语。既然我不打算用兵,去了齐国也毫无益处,只会徒添麻烦。忽而忆起有件事还未曾和他提过,便道:“对了。六年前刘邦出征英布前夕,我在关中曾与师兄见过一面。”
闻言,仲云的眼瞳亮起了光。掩不住满目的欣喜,他急促问道:“那么你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在筹划些什么?”
见状,我不置可否地叹了口气,回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仲云,告诉我,岐山顶上你发动桃花迷瘴时,看到了什么。”
他错愕了一瞬,自知瞒我不过,脸色灰暗了下去:“海。”
果然……仲云曾因心死自坠于深海,从此连瞳孔都被染成了海的颜色。他和我一样是桃树化妖,只需驱动术法即可让周身散发出摄人心魄的瘴毒,轻易取人性命。但与此同时,施法者也会在自己内心埋藏至深的伤痕面前无处遁形,很容易被引入迷途,丧失本性。
“数百年了,你还无法释怀吗?当初师兄将你从海中救出,就是不希望你永远沉沦进去。”
湛蓝色的眼睛执拗地回瞪着我:“恕我无礼。释怀与否是我个人问题,与张兄无关。”
“若站在你面前的是我师兄,你也会说和他无关吗?”
他平淡的表情微微波动了一下,很快又归于沉寂。我没有继续逼问他,起身合上了窗。多年不见,仲云的术法长进不少,心术修为还稍显不足。河上公对他这个宝贝徒儿视若掌上珍珠,宠溺过甚,对他来不知是福是祸。
“我既不知他人在哪里,也不知他欲行何事。那日他同我说若是没有去处,可去代国寻他的弟子。我相信他,仅此而已。”
从南部的长沙到极北的代国晋阳,以我和仲云的脚程来算,若施展起身法,不需要多久。可我们却选择坐船和骑马,一路缓缓地驱驰过去。沿湘江入洞庭湖渡江,过河一路向北,经雁门关,再越恒山。耳畔充斥的人声从纤细婉转的南方腔调变到夹杂着胡语的粗犷北话,眼前景物也从草木葱荣转为白雪皑皑,仿佛一连走过几个时季。从关中蔓延过来的遮天密云,至这偏远之地,多少也散去一些。雨停的时候,偶尔会露出一两块蓝白色的天空。
我没有观景的兴致,却仍旧在观景。望着远山上环绕的烟云,望着断崖边附着的青苔,望着旅人马蹄下激起的碎石尘土,望着路边赌客掷下的荚钱筹码,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望见。
遮于眼前的浓厚迷雾,散去时,才发现直至天际都只一片空洞惨白。水中映出的是自己,却不意味你当真融入其中。
千百年间改变的是什么,挽留住的又是什么?有哪一条如你所愿了?你所愿的,是否存在过呢?日后,还可能存在吗?
这些,你如今可是清楚了?
作为国都的晋阳简简单单,或说是稍显破落,自不能和长安洛阳相提并论。这里生活的人们没有身着锦衣,没有神经质般的猜忌紧张,也没有遇到官兵时习惯性地瑟缩惶恐。见我们两个大冷天还身着素服单衣的外乡人在城门口徘徊,非但没远远避开,反而毫无防备地上前招呼,热情地为我们指明通往王府的路,甚至愿意亲自领我们过去。
我还在错愕间,就已被不知名的热心人带到了王府门口。
礼貌地道谢,对方却只是哈哈大笑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对我念叨了一连串大冷天不能穿得这么单薄年轻人要多吃些才不会如此瘦弱云云,说罢转身扬长而去。
未及给出的金钱握在手心,硌得我生疼。是我太久没体会过人情了,几乎忘记如何不用心计去揣测他人的意图。也许这趟北行,会获得比想象中更大的收获。
入王府,求见代王,道明来历。听我道出「蒯彻」二字,未及束发之年的代王从坐榻上一跃而起,紧紧拉住我的手进了内室,询问他老师的情况。
我心下忽觉有趣。师兄最不擅长的就是与人相处,但所有和他相处过,见过他真正面目的人,都会被他折服,不知是何道理。
这个所谓为他折服的人,大概也包括我在内。
得知我对师兄的近况也不甚了解,代王显得十分忧心。命下人为我们收拾出住处后,又让王舅薄昭将我们带去府院深处,说是王太后也想与我们见上一面。入了王太后所居的西房,才发现帷幕之后,竟是认识的人。
昔年身着大一号的男子军服,惊慌狼狈地冲进议室,直言不讳冲撞汉王的纤弱少女,如今已成为体态端庄,喜怒不形于色的一国之母,只有眼中闪动的刺人光亮依旧如故。
那是和师兄画中常见的那名女子一般无二的光亮。
屏退左右,连仲云和薄昭也自觉离开了,只留我和她面对面。轻轻掀开帷幕一角,那女子浅笑言道:“成信侯,好久不见。抑或我现在该称呼你为文成侯?”
我颔首道:“良早已被汉室驱逐在外,太后直呼姓名便好。”
“子房,我有一问,你可愿如实相告?”
“太后若心中早有答案,则无需问我。”
她神色一黯,素手扣住案边,身体微微前倾,仍是不甘地问了出来:“告诉我。在你来看,他所求之事,有几成胜算?”
“他所求之事?”我淡淡一笑,“太后指的是什么?摧毁九鼎?亦或是其他?”
她眼神飘忽了一瞬,语气却沉定下来:“他在意识不清之际,曾呼过一名,为「阿玖」。我要知道和她有关的事。”
我心下一跳。以师兄的性情,断不会轻易将阿玖之事讲与人听。真是好敏锐的女子。“太后既欲探知我师兄内心,可否容我冒昧一问?你此行所求,又是什么?”
她垂下眼帘,苦涩言道:“我只希望能救他……”不待她将话说尽,我已轻笑出声。
在她错愕的注视下,我放下先前刻意摆出的矜持,笑看烛台上烛火飞散摇曳:“太后,救人啊,方法很多。活将死之人,帮其完成心中所愿,或是说一些宽慰人心的话,都可能救得了一个深陷困苦的人。但是,这些都救不了他。这是在千年前就注定的,凭你单方面的自作主张可改变不了。”
眯眼去看的话,烛火的光就仿佛扩大开来,烧灼着整片视野,在它之后的一切风景或人,都只能化为模糊的剪影,成为火光余晖的一部分。
他自己也早已知晓,所以才会留下那样的话,让我回想起那件他让我「切记」的事。
“我也是前不久才察觉到———没人能救得了他。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的好。”
“我不信!”太后愤然离席站起,帷幔随着她的动作滑落而下,飘散满地。几欲脱口而出的话,在与我眼神交融的瞬间,又猝然失去了踪影。
长久的静寂,在我和她之间弥漫,却比任何言语都能撼动人心。
她后退一步,抬手扶住了身后的屏风。“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虽然救不了他,但他所求之事,我必助其完成。”我维持着水波不惊的浅笑,“即使要与天地作对也无妨,毕竟我可不是会被几声打雷吓唬住的。”
女子纤长的睫毛闪动了几下,费解道:“看来,我要将同样的问题送还给你了。子房,你所求的又是什么?”
我舒出一口气,喃喃道:“是一种光……”
“光?”
我没有继续回答她。这个问题,她也没有再问第二遍。
行事的理由,真的重要吗?那不是可以记载在史书上,流传下来的要事。与之相关的一切,终究会在世人的记忆中一点点消亡,与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无二。既然如此,又何须在意。
世人的期盼是让这场纠缠世间千年的纷争彻底结束。我会继承几世人对与错的夙愿,摒除所有的恩怨和因果,为这场水之竭画上终符。
至于那些沉寂千年的旧事……只需我一个人记住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