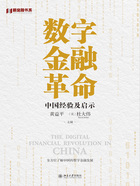
5.数字金融监管重构
谈起对金融行业稳定性的担忧,最不容忽视的就是金融监管,蚂蚁金服暂停上市也是由于监管缺位。由于多种原因,数字金融行业的监管框架尚未完善。第一,监管机构最初对数字金融创新表明了友好的立场,因为它们看到了这些新业务中的普惠价值。第二,目前的监管框架在不同监管部门间是相互独立的——谁颁发许可证,谁就应该负责监管1。目前哪个监管机构应该监管哪个数字金融机构这一问题尚不明确。第三,由于数字金融行业应用先进的数字技术,通过传统的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等监管手段可能难以识别风险。此外,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的一部分,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受政治决策的影响,这通常会导致“运动式监管”——在完全不采取行动和同时采取所有行动之间剧烈摇摆。
当时,蚂蚁金服的数字金融业务整体监管不力,如果IPO按计划进行,监管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蚂蚁金服的业务及其市场估值,因此,停牌对金融行业、资本市场和蚂蚁金服自身都有好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监管机构没有更早地采取统一的监管措施?
数字金融行业监管框架的重构至少应遵循两大原则。一方面,数字金融行业与传统金融行业一样,应全面纳入金融监管,以降低包括过度套利在内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监管标准一致的情况下,监管者也应积极寻求数字金融监管的创新,以平衡效率和稳定性。
详细的监管计划仍在制订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而另一些则难以解决。第一,整个数字金融行业都应遵守相同的监管规则,最好有一个牵头的监管机构。由于金融交易的最大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因此对金融业的监管应该最严格,数字金融也不应例外。同样重要的是,传统金融行业和数字金融行业的监管应该统一,否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套利行为。监管缺失或监管不力均不利于数字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鉴于不同数字金融业务之间可以进行信息共享,数字金融行业政策的协调性比传统行业更重要。中国人民银行自然是统一协调监管者的候选人,但其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的职能仍需加强,且有待制度化。
第二,为了跟上数字金融创新的步伐,监管创新也是必要的。由于数字金融线上交易规模庞大、发展速度惊人,传统的监管方法在管理金融风险方面的效力已经严重不足,更不用说化解金融风险了。监管机构应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来履行监管职责,从而提升其技术能力。当监管机构看到一些创新的好处但不确定其风险和后果时,他们可以采用类似“监管沙盒”的做法,在监管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实验。中国人民银行已于2019年年底启用了中文版“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监管部门也应积极推进监管创新,支持数字金融业快速健康发展。例如,大科技信贷模式非常有效,因为贷款人众多,获得贷款的速度快、质量高。然而,大科技信贷的贷方往往面临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资金供应不足。监管机构可以允许个人和机构远程开设银行账户,鼓励大科技信贷的贷方从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借款,并促进大科技信贷的贷方与传统银行合作,以减弱这一制约因素的影响。
第三,中国迫切需要一套完整的数据使用政策。数字金融业务大多都是大数据驱动的。过去,政府颁布了许多关于数据的法律法规(如保护个人隐私的相关条例),然而,大多数条例要么不够翔实,要么没有通过正确的方法实施。数据滥用这一现象在中国非常常见,在数字金融行业中也不例外。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将数据视为一种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换言之,数据可能进入生产函数、促进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策制定者需要在许多领域制定明确的规则。 (1)谁拥有数据,个人还是平台? 如果两者在数据积累中都有一定的投入和权利,那么决策权和利益应该如何分配? (2)可接受的数据交换方式有哪些? 与劳动力或资本不同,数据可以被多方拥有和使用,理想的交换方式应该能够保护原始数据所有者的权利。 (3)统一的数据标准是进行数据交换的重要条件,但谁来负责制定数据标准,政府还是私营部门? (4)数据的定价机制是什么?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数据就很难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发挥积极作用,数字金融行业也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中国迫切需要针对包括数字金融行业在内的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制定新的反垄断政策。近年来,中国监管机构开始调查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垄断问题。然而,与传统行业不同,数字金融行业的市场份额可能不是判断是否存在垄断的最佳指标。由于数字技术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大科技平台自然而然地成为市场上的“大玩家”。事实上,这是数字金融行业助力普惠金融的技术基础。判断行业是否存在垄断的一个更合适的标准是“可竞争性”——新玩家是否仍然可以进入,并与现有玩家竞争。在中国数字金融行业,可竞争性非常明显。在电子商务领域,淘宝是第一个领先的平台,京东紧随其后。而在最近几年,一个新平台拼多多也正在崛起。在社交媒体领域,虽然微信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一直在与微博竞争,其市场份额也正在不断地被字节跳动蚕食。鉴于数字经济领域的动态特征,特别是商业模式的快速演变,一家企业很难一直保持主导地位和市场力量。在这个阶段,监管政策应该更多地关注竞争的公平性和消费者权益,而不是狭义的市场份额。
第五,从长远来看,当局需要制定数字金融监管的国际战略。尽管一些领先机构开始“走出去”,但中国大多数成功的数字金融业务都在国内。鉴于中国处于数字金融创新的前沿,国际战略的制定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边境限制数字金融交易将变得成本更高、有效性更低。国际战略可以包括有关数字金融创新的经验交流,监管政策的跨国协调,甚至国际数字金融市场的整合2。金融监管机构或许没有能力完全掌控中国数字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但将中国数字金融行业与世界其他地区永久隔离开来本来就是不可取的做法。因此,促进监管者和从业者与国外的同行互动,从而寻求有效的知识共享和业务合作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1 见本书第十一章。
2 见本书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