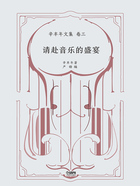
以九部交响曲为中心
贝多芬写了那么多作品,要从何读起呢?无疑的是要以他的九部交响曲为中心了。自从贝多芬写了九大交响曲(大,指其气象与意境之阔大伟观,其实在九部当中也有《第八交响曲》那样篇幅不长的作品),后来的作者像是对“九”这个数字也产生了一种敬畏感,有的作曲家写交响曲,甚至不敢超过这数目了!
然而即使是许多十分喜欢听贝多芬作品的乐迷,怕也不见得对这九部交响曲都那么熟悉、都非常喜爱吧?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便赏遍那九峰中的奇景,领略其气象万千。真正要深入其境,即使对于专门研究贝多芬的音乐家来说也是要穷毕生之力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九部交响曲中挑出特别重要的几部来先读。这也正是一百多年来世界上千千万万贝多芬迷已经不约而同地公选出来的那几部:第三、五、六、九,也即《英雄》《命运》[2]《田园》《合唱》这四部交响曲。
在这几部交响曲之中,人们听起来最容易入门也最感亲切的,无疑是《田园》了。《英雄》由于它有个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联系在一起的佳话,对许多人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吸引力。实际上,要想真正把这部作品听出头绪也听出些意思来,是需要相当认真地反复多次倾听的。至于《命运》,虽然那整部作品的主旨、构思都似乎不难把握,但也绝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么好理解,只有严肃地听过许多遍之后,也许才可能发现更多的意思,引发更深的思索。再说到《田园》,相对其他几部而言诚然是平易近人,可是我们也绝不可把它来同一般的“音乐风景画”等量齐观。如果比作绘画的话,它也是像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杰作那样耐玩的。
以上这三部作品听得相当熟悉,熟到了一听见上文便在脑海里自动准备好迎接下文的程度。(卢那察尔斯基是一位渊博的通人,他形容得绝妙,说这犹如水在沟渠之中自在地流动一般。)之后,我劝你再去倾听另外的五部交响曲,即第一、二、四、七、八。在已熟悉的前几部交响曲的对照之下,你就会发现新天地。你会惊叹不已:原来贝多芬胸中还有那么多话要说!
他的《第一交响曲》尽管还显得有毛头小伙子初涉人世的稚气,但已从他的前人海顿、莫扎特的身影下走了出来,而且跨出了好几大步了。等你以后听了莫扎特的交响曲之后就会对此有深刻的感受。
《第二交响曲》便完全是这位波恩英俊少年的自家面目了。这部交响曲(特别是其中的前两个乐章)中的力与美,犹如江河般奔腾向前的那股气势,叫人不能不想起他所处的那个壮丽的时代,那个风云扰攘“狂飙突进”的欧洲。从音乐中可以看到一个英气勃勃、胸中有无限激情只待倾吐的青年贝多芬。在九大交响曲中,《第二交响曲》也许还是不少听众尚未充分发现其美妙的一部作品。《第四交响曲》中细腻而又深沉的抒情味,《第七交响曲》的酒神气质,《第八交响曲》中的幽默口吻,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感受的。然而如想对这几部作品有深入一层的领略,仍然有待于反复倾听,也有赖于你在文艺、美学方面的眼界的扩大与知识趣味的丰富。即便不谈内容,仅从乐艺欣赏的角度来说,它们之中也有发掘不完的迷人的细节。
一个乐迷,假如他已经用心倾听了贝多芬的前八首交响曲并有所感受,是否就可以说他已经领略到贝多芬的伟大深刻了?回答是:远远不够!因为,还有一座俯视群峰,“一览众山小”的最高峰,西方交响乐文化中的最高一峰。如果我们无缘认识它而不幸死去,那对于一个乐迷来说仍然是大可悲哀之事!反之,即使你终其一生没听多少好音乐却有幸见识了《第九》,那么在临终之际也可以在心里默唱着《欢乐颂》,想着那篇极其真挚、崇高的慢乐章,含笑而逝,也不虚此生了!
生于今日的乐迷无论如何不幸,至少在可以饱听《第九》一事上远比19世纪的人幸运,甚至可以说我们虽是凡人却比那时的音乐家还要幸运。今日人们可以天天听,一日听几遍,尽情享受《第九》赐予的深沉的震撼,体验它引发的精神的高扬,灵魂的战栗、沉思、憧憬、渴望。而可怜的19世纪人,他们是生于唱片时代之前的人,他们只能上音乐会去听《第九》。可是音乐会里虽然经常翻来覆去演奏许多平庸但却时髦的作品,《第九》这样的演奏起来吃力不讨好的伟大作品则是很难得有机会一演的。即使是在德国莱比锡那样的爱乐之城,即使有门德尔松那样的大师为提倡高尚音乐文化,尤其是巴赫和贝多芬的作品不遗余力,当地也有格万豪斯乐队那样完美的乐队:尽管有这一切,当年那地方要听《第九》也是难。演奏《第九》是难得的盛事,有些人甚至十年中也难躬逢其盛!所以向往这部伟著的爱好者只好在自己家里的钢琴上弹弹它的钢琴改编谱了。就连托尔斯泰与其爱乐且多才的夫人也不得不如此。
所以,要用简略的字句来介绍这篇人间绝唱之美妙,是不可能的。当你诚心诚意地顶礼膜拜之后,也自然会体会到,想用文字语言来谈论《第九》,不免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