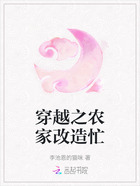
第5章 建设了村农仓
随着推广三步的开展,村里的人都开始采用新方法种田了,全村只有几家特别固执的人家不愿意更换新技术,其中最难啃的骨头就是周老爷家。
李小小三顾茅庐,周老爷就是不肯,最后还提出一个赌约:周家划出两亩地,一亩按老法子种,一亩按她的方法种,秋收时见分晓。如果新法比老法强,秋收后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收成,成立“村农仓“,防备荒年。但是,如果新法不如老法,她则赔周家十石粮食!
这个豪赌震动了全村。连最反对的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丫头的胆识。
####
麦子抽穗时,李小小开始推广间作法。没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技术,也遭遇了重重困难。
第一个问题是品种搭配。村里李四叔不听劝告,硬要在麦地里间种高秆黑豆,结果豆秧把麦子都遮住了,导致两样作物都长不好。
“我就说这法子不行!“李四叔气得直跳脚。
第二个问题是管理不当。钱家媳妇太勤快,看到豆秧上有虫,就喷了大量草木灰水,结果连麦子也烧伤了。
最棘手的是病虫害新问题。由于改变了田间小气候,往年少见的豆荚螟突然暴发,好几家的豆子被害虫吃得千疮百孔。
“都是这妖女害的!“周老爷趁机煽风点火,“好好的地非要乱搞,现在遭报应了吧!“
面对危机,李小小展现出超乎年龄的沉稳。她白天钻在田间观察虫情,晚上挑灯查阅记忆中的农业知识(虽然能想起的有限),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首先是生物防治。她带着孩子们去抓瓢虫、草蛉等益虫,放到受害田里。其次是物理防治,用竹片和纱网做了简易防虫罩。最后是科学用药,教大家用烟叶水、辣椒水等土法农药,既有效又不会造成药害。
为了普及正确的间作技术,她发明了“三看“法则:
一看高矮——矮秆配高秆;
二看根系——深根配浅根;
三看季节——早熟配晚熟。
还编了个顺口溜:“麦豆好朋友,高粱要单走;芝麻脾气怪,最好自己待...“
渐渐地,间作田开始展现出优势。特别是麦收后,豆子正好进入盛长期,充分利用了阳光和空间。到了盛夏,别人家的地已经闲下来,间作田里却依然郁郁葱葱。
####
秋风送爽时,李家村的田野变成了金色的海洋。沉甸甸的麦穗低垂着头,饱满的豆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周老爷站在田埂上,一双浑浊的老眼死死盯着自家的麦田。麦穗稀疏,秆细如筷,和旁边李家那沉甸甸、金灿灿的麦浪相比,简直像是两个世界。
他攥紧了手中的拐杖,指节发白,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硬石头,半晌说不出话来。
“周老爷,您看……“管家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咱们的麦子,怕是……“
“闭嘴!“周老爷猛地一杵拐杖,泥水溅到了袍角上,但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他的目光缓缓移向不远处——李小小正带着几个村民在田间测产,笑声远远传来,刺得他耳膜生疼。
他输了。
而且输得彻彻底底。
赌约是他亲口应下的,全村人都见证着。如今李家田里的麦子穗大粒满,豆荚饱满得快要炸开,而他的田里,麦秆细弱,豆秧上爬满了虫眼,产量连李家的一半都不到。
“老爷,咱们……“管家欲言又止。
周老爷深吸一口气,终于颤巍巍地迈开步子,朝李小小的方向走去。
围观的村民见状,纷纷让开一条路,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
“周老爷这是要认输了?“
“啧啧,活了大半辈子,被个小丫头比下去了……“
“嘘!小声点,别让他听见!“
周老爷充耳不闻,只是死死盯着前方。他的脚步越来越慢,最后停在了李小小面前。
李小小正蹲在地上数麦穗,察觉到阴影笼罩,抬头一看,不由得一愣。
“周老爷?“她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麦壳,神色平静。
周老爷的嘴唇抖了抖,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他盯着李小小看了许久,终于,缓缓弯下腰,深深作了一揖。
“老朽……服了。“
四个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却重若千钧。
全场寂静。
李小小眨了眨眼,随即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伸手虚扶了一下:“周老爷言重了,种地这事,本就是互相学习。“
周老爷直起身,脸色依旧铁青,但眼神里的倨傲已经消散了大半。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丫头,你那'村农仓'的主意……算我周家一份。“
李小小眼睛一亮:“周老爷愿意加入?“
周老爷冷哼一声:“愿赌服输,我周家还不至于赖账!“
说完,他转身就走,背影僵硬,但脚步却比来时轻快了些。
村民们面面相觑,随即爆发出一阵欢呼。
连周老爷都低头了,这垄作法和间作法,还能有假?
####
第二天天还没亮,李家院子外就已经挤满了人。
不仅是本村的,连隔壁王家村、赵家沟的农户都连夜赶了过来,生怕错过学新技术的机会。
“小小!小小!快开门啊!“
“我家明年也想种垄作田,教教我呗!“
“还有我!我家地肥,能不能豆麦间作再加点别的?“
李小小被吵醒,揉着眼睛推开门,差点被眼前的阵势吓到——院外围了至少五六十人,个个眼巴巴地看着她,手里还拎着鸡蛋、腊肉、新磨的面粉,显然都是来“拜师“的。
她愣了一瞬,随即笑了:“大家别急,一个个来!“
很快,李家院子变成了临时学堂。李小小站在磨盘上,手里拿着自制的竹教鞭,指着墙上挂着的示意图,大声讲解:
“垄作的关键有三点——垄高、沟宽、行距!记住了,垄高一尺二,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沟宽一尺,方便排水;行距根据作物调整,麦子八寸,豆子一尺……“
村民们听得认真,有的还掏出炭笔在小木板上记笔记,生怕漏掉一个字。
李小小讲完理论,又带大家去田里实操。她亲自示范怎么用竹尺量垄距,怎么用曲辕犁起垄,怎么用点播器下种。
“这播种器真好用!“王家村的老汉试了试,惊喜道,“再也不用担心撒种不均匀了!“
“小小,这除草耙能站着干活?我来试试!“赵家沟的年轻后生抢过竹耙,在垄沟里划拉几下,杂草连根带起,轻松得让他瞪大眼睛,“神了!这比弯腰锄一天省力多了!“
李小小笑眯眯地看着众人,心里成就感满满。但她很快发现一个问题——人太多了,她一个人根本教不过来。
于是,她灵机一动,把最早学会技术的几户人家(比如张老汉、李大牛)拉出来当“助教“,分组教学。
“张叔,您负责教起垄!“
“大哥,您来教间作搭配!“
“王婶,您带妇女们学播种器的用法!“
很快,李家村的田野上,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教学场景。老人们蹲在地头研究垄高,年轻人比赛谁起垄又快又直,孩子们跑来跑去递工具,连往日最懒散的闲汉都凑过来学手艺,生怕被落下。
这是李家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盛况。
####
秋收结束后,李小小召集全村人,在打谷场上开了个大会。
“各位叔伯婶娘,“她站在碾盘上,声音清亮,“今年的收成,大家都看到了吧?“
“看到了!“众人齐声应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那我的条件,大家还记得吗?“
场上安静了一瞬,随即有人喊道:“记得!十分之一的收成交'村农仓'!“
李小小点头:“对!这粮仓不是给某个人的,是全村共有的!遇上荒年,可以借粮度日;谁家遭了灾,也能应急。“
她的话掷地有声,村民们交头接耳,多数人点头赞同,但也有少数面露犹豫。
这时,周老爷突然拄着拐杖站了起来。
全场瞬间安静。
“我周家,出二十石。“他沉声道,“其中十石是赌约输的,另外十石,是我自愿捐的。“
此言一出,满场哗然。
周老爷环视众人,缓缓道:“这些年,我仗着家底厚,没少为难乡亲。今年这场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地种得好不好,不在年岁长短,而在肯不肯学新东西。“
他转向李小小,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这丫头有本事,我服气。'村农仓'是好事,我周家支持。“
这番话像是一锤定音,原本犹豫的人家也纷纷表态:
“我出五斗!“
“我家出一石!“
“我们兄弟俩合出两石!“
李小小眼眶微热,她没想到周老爷会带头支持,更没想到村民们如此齐心。
很快,在村长的组织下,“村农仓“正式成立。粮仓建在村子中央,由厚实的青砖砌成,仓顶铺着防水的竹瓦,门上挂着三把锁——钥匙分别由村长、周老爷和李小小保管,必须三人同时到场才能开仓。
开仓那天,全村人齐聚一堂。当第一袋粮食倒入仓中时,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很快,掌声响彻云霄。
李小小站在人群中,看着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踏实感。
这不仅仅是一座粮仓,更是全村人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