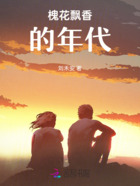
第17章 伯乐
一九八五年六月的第一个周日,姜晓兰抱着小程梅在院子里晒太阳。婴儿的皮肤在阳光下近乎透明,能看见淡蓝色的血管。早产一个月的孩子比一般新生儿瘦小,但这两周总算长了点肉,小手攥着母亲的手指,力道让人惊喜。
“梅梅,看这里。“姜晓兰晃动着彩色布偶,婴儿黑亮的眼珠跟着转动。医生说过,孩子的追视能力不错,但早产儿的发育要持续观察。
院门“吱呀“一声开了,程卫东拎着两条鲫鱼走进来,身后跟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那人约莫五十出头,灰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浅灰色中山装洗得发白,但整个人透着一股书卷气,像从老照片里走出来的学者。
“晓兰,这位是省理工大学的周教授。“程卫东介绍道,“专门来看建军的。“
姜晓兰刚要起身,周教授连忙摆手:“别动别动,小心孩子。“他的目光落在小程梅身上,突然变得异常柔和,“多大了?“
“刚满月。“姜晓兰下意识把孩子搂紧了些。自从王校长来过之后,这已经是第三拨“慕名而来“的大学教授了。
程卫东把鱼放进厨房的水盆,擦了擦手:“建军在车间调试新机器,我去叫他。“
周教授却拦住他:“不急,我先看看你们厂。“他的视线扫过院子里晾晒的图纸和零件,突然蹲下身,拾起一块画满公式的草稿纸,“这是谁算的?“
姜晓兰探头一看,认出是张建军的笔迹:“应该是建军的演算稿。“
“精妙的简化方法...“周教授推了推眼镜,手指微微发抖,“这种思路,我只在一个人那里见过。“
正说着,张建军从后院转出来,工作服上沾满油污,右脸的伤疤在阳光下泛着红光。看见周教授,他猛地站住,手里的扳手“咣当“掉在地上。
“教...教授?“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周教授缓缓起身,镜片后的眼睛湿润了:“小张,真的是你。“
一阵风过,院子里的槐树沙沙作响,落下几片白色花瓣。张建军像尊雕塑般僵立着,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惶恐,最后定格在某种释然上。
“您怎么找到这里的?“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科技日报》上看到关于你们厂的报道,提到了一个'自学成才'的技术员。“周教授向前走了两步,“描述让我想起七年前失踪的那个最有天赋的学生...“
姜晓兰和程卫东交换了个眼神。他们猜想过张建军可能上过学,但没想到竟是名校高材生!
“进屋说吧。“程卫东打破沉默,“我去泡茶。“
狭小的客厅里,周教授捧着茶杯,目光始终没离开张建军:“当年你突然退学,我们都以为...“
周教授突然抓住他的手:“现在呢?还想学数学吗?“
张建军愣住了。姜晓兰看见他眼中闪过一丝渴望,但很快又黯淡下去:“我现在是槐香厂的技术科长,东哥和姜老师对我有恩...“
“谁说报恩和求学不能兼顾?“周教授从公文包里取出份文件,“省理工新设的职工大学,专门为你们这样的青年才俊开设的。每周两天课,其余时间可以在职工作。“
程卫东接过文件快速浏览:“这...这不正好吗?建军,你去!厂里全力支持!“
张建军的目光在三人脸上来回游移,最后停在姜晓兰怀里的小程梅身上。婴儿不知何时醒了,正睁着乌溜溜的眼睛看他。
“我...我得想想。“他最终说。
送走周教授后,张建军把自己关在车间里,直到深夜都没出来。程卫东去送饭时,发现他正对着一台半成品机器发呆,手里捏着张泛黄的老照片。
“东哥,“他没抬头,“你知道我为什么对农机这么执着吗?“
程卫东在他身边蹲下,看见照片上是个穿粗布衣裳的农村妇女,站在麦田里微笑。
“我娘。“张建军轻声说,“我考上大学那年,她为了挣学费,去帮人收割,结果被脱粒机绞断了手...感染没的。“
程卫东的喉咙发紧。他想起张建军设计的安全装置,那些被沃罗宁称赞的巧妙结构,突然明白了一切。
“周教授是个好人。“张建军继续说,“当年那本禁书,其实是他偷偷借给我的。出事那天,他冒着风险去求情,差点连累自己...“
夜风从车间的铁皮缝隙钻进来,吹得工作台上的图纸哗哗作响。程卫东想起自己当年为了照顾母亲放弃高考的经历,突然觉得命运像个圆,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闭合。
“去吧。“他拍拍张建��的肩,“学好了回来,咱们造更多安全的机器。“
三天后,张建军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着周教授去了省城。临走时,他把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交给程卫东:“东哥,这是我这些年的技术心得,还有K-7M的改良方案。“
程卫东翻开扉页,上面工整地写着:“给我最信任的兄长——程卫东。张建军,1985年6月5日。“
姜晓兰抱着小程梅来送行。婴儿似乎感应到什么,突然伸出小手,抓住了张建军的一根手指。年轻人愣住了,眼圈瞬间变红。
“梅梅喜欢你。“姜晓兰笑着说,“记得常回来看她。“
张建军郑重地点头,转身上了周教授的自行车后座。两个身影在晨光中渐渐远去,融入了通往省城的黄土路。
夏至这天,县里来了通知:槐香农具厂被评为“省乡镇企业示范单位“,获得了一万元奖金和免税一年的政策。更令人惊喜的是,沃罗宁牵线的中苏技术合作项目正式获批,首批二十台样机的订单已经到位。
庆功宴上,程卫东喝得满脸通红。姜晓兰因为哺乳期不能喝酒,抱着女儿坐在角落,看工人们闹哄哄地拼酒。老马师傅喝高了,拉着新来的学徒讲张建军如何用一根铁丝修好进口机器;李婶则不停地往姜晓兰盘子里夹菜,念叨着产妇要补身子。
“程厂长!“邮递员突然出现在门口,挥着一封挂号信,“省城来的!“
程卫东拆开信封,里面是张建军的入学通知书和一张便条:“东哥,已报到。周末就回来帮忙。另:周教授看了K-7M图纸,说有个想法...“
姜晓兰凑过来看信,怀里的程梅突然“咯咯“笑起来,小手在空中抓挠,像是要抓住那些从信封里飘落的槐花花瓣——不知何时,张建军在信纸里夹了几朵风干的槐花。
夜深了,宴席散去。程卫东和姜晓兰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夏夜的星空格外明亮,银河像一条缀满钻石的缎带,横贯天际。
“晓兰,“程卫东突然说,“我打算用那笔奖金办个幼儿园。“
姜晓兰惊讶地看着他。
“工人们的孩子没人带,影响干活。“程卫东解释道,“再说...梅梅以后也要上学前班。“
月光下,姜晓兰看见丈夫眼中有泪光闪动。她知道,这个决定不仅仅是为了工厂,更是为了那些像张建军一样,本该拥有更好起点的孩子。
小程梅在母亲怀里睡得香甜,嘴角还挂着奶渍。远处,农具厂的轮廓在夜色中巍然矗立,新安装的“槐香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招牌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