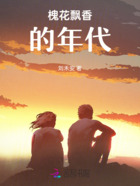
第23章 并蒂莲
---
青山县·程家老宅
程卫东蹲在父亲留下的樟木箱前,指尖拂过箱角斑驳的蓝漆。那是当年农机站统一配发的颜色,如今已褪成一片模糊的灰蓝。
“你爸临走前说,这箱子要等你三十岁才能开。“程母坐在藤椅上,枯瘦的手指捻着佛珠,“里头装的不是什么金银细软,是祸根。“
铜锁早已锈死,程卫东用螺丝刀撬开时,铁屑簌簌落在青砖地上。箱子里整整齐齐码着十几本工作笔记,最上面那本封皮上印着“哈尔滨军工学院1963-1964年度技术研讨纪要“。翻开扉页,一张泛黄的苏联邮票粘在角落,列宁头像下方有人用钢笔描出极细的虚线。
程卫东对着煤油灯举起纸张,光透过邮票背面显出密麻麻的小孔——是 Morse电码。他心跳骤然加快,父亲生前是全县唯一的电报员。
窗外突然传来树枝刮擦声。程卫东猛回头,看见月光下张建军惨白的脸贴在玻璃上,右脸的疤痕被窗棂分割成诡异的几何图形。
“东哥,“张建军的声音隔着玻璃闷闷的,“我娘坟前...多了束新鲜槐花。“
---
省城医院·姜晓兰母亲家
缝纫机踏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姜晓兰跪在母亲生前最珍视的“蝴蝶牌“缝纫机前,螺丝刀插进暗格缝隙的瞬间,她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暗格只有巴掌大,里面躺着本焦边的笔记本。第一页贴着张剪报——1965年《黑龙江日报》关于“中苏青年技术交流会“的报道,照片里站在苏联专家身边的姑娘梳着两条长辫,正是年轻时的姜母。
翻到第七页,姜晓兰的指尖突然颤抖起来。1968年9月15日的记录被大片褐红色污渍覆盖,勉强能辨认出“淬火油““替换““张思远“几个词。页脚画着朵并蒂莲,墨迹晕染处现出两个指纹,一大一小,像母亲牵着幼时的她。
床头柜上的药瓶突然滚落。姜晓兰回头,看见程梅不知何时醒了,正用异常清明的眼神望着她,小手在空中抓挠,仿佛要抓住那些飘散的尘埃。
“姥姥...“孩子突然吐出这个从未教过的词。
---
和平饭店·匈牙利客商套房
张建军盯着茶几上的照片,太阳穴突突跳动。照片里两个穿海军领童装的男孩站在哈军工宿舍楼前,一个右脸有月牙形疤,一个左手缺了无名指——正是他自己的手。
“这是1960年夏天。“安德烈的中文突然变得流利,“你父亲把你哥哥送去苏联时,你母亲哭晕在火车站。“他转动左手戒指,露出内侧刻着的“HB65“编号,“我们找了他二十年。“
沃罗宁默默推过一杯伏特加。酒液里浮着朵小小的干槐花,张建军突然想起母亲总在月圆夜给他喝的“安神汤“,也是这个味道。
录音机突然自动播放,磁带嘶嘶声中响起陌生又熟悉的童声:“我叫张卫国,今年七岁,我的双胞胎弟弟叫张建军...“
窗外电闪雷鸣,暴雨冲刷着玻璃上张建军扭曲的倒影。他的影子分裂成两个,一个穿着劳改农场的破棉袄,一个套着笔挺的苏式军装。
---
三线交汇·暴雨夜
程卫东破译的密码指向哈尔滨老城区的一座教堂地下室;姜晓兰在母亲笔记里发现的地址却是郊外的废弃钢厂;而张建军得到的坐标,竟是青山村后山的乱葬岗。
三人在县医院走廊相遇时,程梅正发着高烧说胡话,不断重复着“淬火油““两个爸爸“之类的字眼。值班医生递来的化验单上,Rh阴性血型栏被红笔圈了三次。
“去后山。“程卫东突然说,“我爹临终前念叨过,乱葬岗有棵歪脖子松。“
姜晓兰从药盒夹层抽出那张染血的笔记:“这上面说...真正的配方藏在'双生的心脏'里。“
张建军摸了摸右脸的疤,想起录音带里最后那句话:“记住,你兄弟的疤在相反位置。“
---
暴雨中的乱葬岗
歪脖子松的树洞里,铁盒早已被腐蚀得不成形状。程卫东挖出它时,一道闪电劈亮盒盖上并蒂莲的浮雕——左边花瓣缺了一角,和姜晓兰母亲笔记里的图案一模一样。
盒里只有半页被血浸透的《真理报》,1968年9月16日的头版头条:《中苏友谊万古长青》。报纸背面用槐花汁写着几行字:
“卫国带去苏联的是假配方
真配方在连理枝的年轮里
找到我们的女儿“
张建军突然跪倒在地,雨水冲开他衣领——锁骨位置赫然露出个陈年烙印:HB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