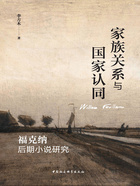
导论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研究成果丰硕,关于福克纳作品,无论是意识流手法、叙述视角、语言风格等形式研究,还是性别、种族、阶级、生态、地域等主题阐释,均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纵览福克纳学术史,学者们历来注重及时总结已有成果,例如美国学者哈古德(Taylor Hagood)近期出版的《追随福克纳:对约克纳帕塔法建造者的批评回应》(Following Faulkner: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Yoknapatawpha’s Architect,2017)追溯了近百年来福克纳研究领域百余部专著的主要观点与影响,成为一部简洁、有力的学术史综述。另外,福克纳研究文献大致有书报评论、学术论文和文献目录等类型。针对书评的甄选与总结主要有三部:巴塞特(John Bassett)的《福克纳批评遗产》(William Faulkner:The Critical Heritage,1976)、英奇(M.Thomas Inge)的《福克纳当代评论》(William Faulkner:The Contemporary Reviews,1995)以及法格诺利(Nicholas Fargnoli)的《福克纳文学指南》(William Faulkner:A Literary Companion,2008)。上述三部著作均按照时间顺序收集整理了福克纳作品出版之后的代表性书评,但巴塞特一书以福克纳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为分水岭,将1950年作为收录经典文献的终点,他认为获奖之后各类评论喷薄而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批评本身的客观性。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年,旨在总结研究成果的《福克纳评论二十年》(William Faulkner:Two Decades of Criticism)一书由霍夫曼(Frederick J.Hoffman)和维克里(Olga W.Vickery)合作编选出版,由此开启了另一种学术批评范式——每隔十年做一次总结。后来二人编选的《福克纳评论三十年》(1963)、瓦格纳(Linda Welshimer Wagner)的《福克纳评论四十年》(1973)和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的《福克纳评论六十年》(2002)等相继出版。此外,巴塞特还及时对世界范围内的福克纳研究文献目录进行总结,先后编纂出版四部散篇清单(William Faulkner: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Criticism,1972;Faulkner: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Recent Criticism,1983)或注释目录(Faulkner in the Eighties:An Annotated Critical Bibliography,1991;William Faulkner: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 Since 1988,2009),为福克纳学术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仅最近出版的这本书即收入1988—2007年世界范围内的不完全统计论著条目、博士学位论文及其他专题论文共计3074条。
福克纳创作的全部作品中,《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1936)和《去吧,摩西》(Go Down,Moses,1942)等小说受到学界关注较多,而1942年之后陆续出版的《坟墓的闯入者》(Intruder in the Dust,1948)、《骑士的策略》(Knight’s Gambit,1949)、《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 Nun,1951)、《寓言》(A Fable,1954)、《大森林》(Big Woods,1955)、《小镇》(The Town,1957)、《大宅》(The Mansion,1959)和《掠夺者》(The Reivers,1962)等作品长期以来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现有的评论也大多对这些后期作品持否定态度,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特别是1950年获得前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福克纳表现出才思枯竭、动力衰退的疲态,作品的思想性和写作手法均乏善可陈。[1]《去吧,摩西》出版之年(1942)对于福克纳的文学生涯来说非常重要。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放弃之前外交领域一直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正式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大大激发了福克纳的参战热情,尽管后来的结果表明梦想难以成真。当时,福克纳正忙于创作《去吧,摩西》中那篇著名的《熊》(“The Bear”),但事有不顺。12月2日,他向出版社致函解释延迟交稿的原因:“可写之处比我预想的多出很多,这或许能够成为令我引以为豪的章节,需要耐着性子去写,反复修改才能写好。”[2]1942年初,陪伴福克纳家族四代人的黑人大妈卡洛琳·巴尔(Caroline Barr)去世,福克纳亲自主持了葬礼,把即将出版的小说题献给这位世纪老人。5月11日,《去吧,摩西》由兰登书屋正式出版[3],成为继《村子》(The Hamlet,1940)之后又一部重要小说。于国、于家、于福克纳本人,1942年都是标志性的一年。
本书辟出《去吧,摩西》作为福克纳写作生涯的分水岭,主要考虑如下。这部小说深刻揭露了南方白人特权家族的种族主义罪恶,确立了后期多部作品人物的家族关系框架和叙事范式。从故事层次上看,麦卡斯林家族在福克纳塑造的南方贵族世系中延续最久、支脉最广、涉及的社会问题最多。早期福克纳研究较多关注作家的道德关怀,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变迁折射社会转型期美国南方家族的情感结构和内在矛盾,然而这种由点及面的研究路径并未对小说人物家族背景在叙事中的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福克纳的后期作品有意编织了异常繁复的家族关系网,人物个体与南方社会的命运交相呼应,凸显出家族的地域性、历史性和多变性特点。本书有意避开学界较为关注的前期小说,排除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寓言》[4],选取《去吧,摩西》《坟墓的闯入者》《骑士的策略》《修女安魂曲》《大森林》《小镇》《大宅》《掠夺者》共八部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为研究对象。同时,结合对福克纳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重要散文和公开演讲的深度解读,本书旨在探讨福克纳后期作品中家族关系对人物的性别、种族和阶级身份塑型的影响,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复杂多元的南方社会文化氛围中人物的身份认同机制。
身份或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是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个人与社会文化的认同问题。在霍尔(Stuart Hall)看来,现代人的身份表现出“去中心化”的特质:主体在不同时段内具有相互矛盾、暂时性的身份,鉴于外部文化世界不断“增殖”,身份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5]由此看来,福克纳的小说人物离不开美国南方家族背景及相互关系,而内战以来南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种族、阶级乃至性别身份均经受着新现实、新文化、新思想的冲击。既然身份本身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福克纳的小说人物对南方记忆与社会现实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例外,正如《押沙龙,押沙龙!》结尾处昆丁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恨[南方]……我不。我不!我不恨它!我不恨它。”[6]
国家认同的观念是随着作家对家族题材的深入开掘逐渐显现出来的。囿于美国南方在内战中的败绩,福克纳塑造的很多人物——尤其是亲历战争的沙多里斯、康普生和萨特潘等南方显赫家族的先祖们,对总体的美国形象并不认同,这种敌对思维一直存在,并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后世。相应的,内战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南方人物在与北方社会的全面交往中也是不被认同的,这种地域身份符号突出表现在浓重口音、颓废意识、小农思维、强烈乡愁等各个方面,在南方之外的美国人士看来他们是经济落后、思想落伍的一个社会群体。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更多的南方人走向北方、走出国门,他们以更为广阔的地理和心理视域反观美国南方,开启以家族背景为基础、融合强烈南方地域文化色彩、兼及美国总体形象的心理建构过程。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南方人士受爱国主义感召,更为积极地融入美国国家形象的维护与塑造中,福克纳小说中的人物以保家卫国为己任,强化了内心的国家认同感。本书探讨的国家认同,即是以时代背景为参照,通过与福克纳前期创作进行对比,发掘后期作品中故事人物心理层面上对南方历史和家族记忆的深刻反思,厘定他们对国家形象及文化遗产的观念转变历程。也就是说,人物的国家认同与家族关系及其文化遗产是相互建构的。
恰是在对社会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审问和反思中,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历经内战、重建、进步主义运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等诸种重大事件之后,人物尝试走出历史记忆的阴影与偏狭的地方主义思维,融入更为宽宏的国家认同语境。放眼福克纳的一生,他的文学生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冷战国际秩序确立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结束,其间产出的十九部小说既是对这段历史的折射,也以作家的方式深刻影响了美国南方乃至整个美国社会。
一 福克纳创作生涯及学术史分期
自密西西比大学读书期间发表第一个短篇故事《幸运着陆》(“Landing in Luck”,1919)开始,到1962年6月《掠夺者》出版,福克纳的创作生涯跨越四十余年,涉及诗歌、短篇故事、小说、电影剧本等不同文类。乡土题材贯穿始终,对南方贵胄家族历史变迁的刻画更是大部分小说的共有母题。1956年春接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记者斯泰因(Jean Stein)专访时,福克纳如此评论自己的写作生涯:
创作《士兵的报酬》时我觉得写作很有趣,接着又发现不仅每一本书都要有所规划,甚至一位艺术家所有的产出或作品都要有规划。写《士兵的报酬》和《蚊群》那会儿,我只是为写作而写作,因为这很有乐趣。从《沙多里斯》开始,我发现自己那片小得像邮票一般的故乡热土更值得写,甚至我一辈子都写不完,当真实升华为想象之后,我就享有了绝对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上天赋予我的才能发挥到极致。这一想法为我打开了人物的内心宝藏,随即创造了我自己的世界。我可以像上帝一般让这些人物动起来,不仅仅是在空间,而是还在时间中移动。我确实成功实现了让人物在时间中随意穿行,这至少在我看来印证了自己的一个理论,即时间是流动的,除非暂时化身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否则它无法存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曾经”,只有“如是”;如果真有“曾经”的话,那就不会有忧伤或悲痛了。我喜欢把自己创造的世界形容为宇宙中的某块拱顶石,这块石头虽小然而一旦抽身,整个宇宙就会崩塌。我的收山之作应该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末世审判书和宝鉴录,然后就此封笔,宣告结束了。[7]
这段引文突出强调了两点:福克纳的乡土情结和作品的整体规划。“邮票”一说将福克纳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家乡拉斐耶县(Lafayette County)纳入美国的文学地图,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沙多里斯》(Sartoris,1929)[8]被学界普遍视为作家标志性的南方乡土题材小说的滥觞之作。例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曾明确指出,这部小说是“福克纳进入他专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标志”[9]。值得注意的是,福克纳说上述一番话时年近花甲,距小说处女作《士兵的报酬》(Soldiers’ Pay,1926)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1926年之前,福克纳是诗人,经同乡友人菲尔·斯通(Phil Stone)的引荐和资助,出版过一部诗集《大理石牧神》(The Marble Faun,1924)。斯通在福克纳的诗歌创作道路上发挥了导师的作用,但他似乎更在意福克纳的培养之道,以此作为个人“进入文学界的赌注”,竭力占有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诗人。[10]斯通与福克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外溢,这似乎是后者不愿接受的。1926年初,福克纳选择寄居新奥尔良,他的文学写作道路随即发生较大转向:创作体裁由诗歌转向小说,玉成此举的是当时已经享有盛誉的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安德森成为福克纳的第二任导师,他建议踌躇满志的青年福克纳去发掘故乡的潜在文学价值:“你是乡下来的孩子,最熟悉的莫过于密西西比那一小块生你养你的土地了。”[11]安德森所说的“一小块”土地恰是上述福克纳所称“小得像邮票一般的故乡热土!”如果说斯通将福克纳引向诗歌创作,安德森则帮助他发现题材的宝藏,完成整体设计。福克纳承认作品体系中存在一个整体设计,然而这样的设计很可能并不是创作之初即有,而是在后期实践中对同一题材持久而深入发掘过程中逐渐明晰的。
考虑到访谈活动中声音媒介的特殊性,福克纳所说的“沙多里斯”一词颇具含混性——所指既可以是书名,也可作为家族姓氏。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金尼(Arthur F.Kinney)教授曾抛出质疑,我们无法确认福克纳所指的是那部小说还是“沙多里斯家族”。[12]不管是首次发表该访谈的《巴黎评论》杂志,还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园中狮:福克纳访谈录》(Lion in the Garden: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1926—1962,1968),均将这个词视作第一部约克纳帕塔法小说来理解。福克纳本人也曾建议普通读者,应该从“沙多里斯”开始,它是“我全部创作的源头”。[13]美国评论家霍夫曼(Frederick J.Hoffman)早在《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961/1966)一书中明确指出,《沙多里斯》的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是福克纳运用家族传统进行创作的开始。[14]也就是说,约克纳帕塔法小说世界的创立是与福克纳的家族书写同步启动的,首作、乡土题材和家族传统密切交织于一个姓氏。
福克纳接续写出了《圣殿》(Sanctuary,1931)、《曾经有一位女王》(“There Was a Queen”,1933)、《没有被征服的》(The Unvanquished,1938)等小说和短篇故事,完善沙多里斯家族及其成员的故事。同时,《喧哗与骚动》、《夕阳》(“That Evening Sun”,1931)和专为考利(Malcolm Cowley)出版《袖珍福克纳读本》(The Portable Faulkner,1946)一书撰写的《1699—1945康普生家族》(“1699—1945 The Compsons”)等小说、故事或短文,全面塑造了南方另一个种植园显贵——康普生家族。另外,《押沙龙,押沙龙!》再现了萨特潘家族,《去吧,摩西》《坟墓的闯入者》《大森林》《掠夺者》从不同侧面塑造了麦卡斯林家族。以律师加文为代表的史蒂文斯家族则陆续出现于《八月之光》《村子》《去吧,摩西》《坟墓的闯入者》《骑士的策略》《修女安魂曲》《小镇》《大宅》之中,斯诺普斯家族更是贯穿自《沙多里斯》到《掠夺者》的多部小说。这些虚构的南方家族各有特色,又具有融入变迁的共性色彩,合起来构成了完整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the Saga of Yoknapatawpha County)。《袖珍福克纳读本》封套上印有这样的宣传语:“首次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全景呈现密西西比州境内的福克纳神话王国。”
这种创作题材的整体性与统一性赋予作家持久的创作动能。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仍然笔耕不辍,创作完成了五部小说、结集出版两部短篇故事集、参与编创《乱世情天》(The Left Hand of God,1951)和《法老的土地》(Land of the Pharaohs,1954)等电影剧本。加上前一个十年出版的《去吧,摩西》和《坟墓的闯入者》,福克纳在生命的后二十年为世界留下七部小说,仅从数量上看,这种勤奋精神“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15]。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福克纳对安德森颇有微词,在1953年6月《大西洋》刊登的《记舍伍德·安德森》(“A Note on Sherwood Anderson”)一文中,这位导师式人物被称作“只有一两部作品的人”[16],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丝轻蔑。
国内外学者有个基本的共识:福克纳的作品体系具有整体规划。[17]为福克纳赢得首届欧·亨利奖的短篇故事《烧马棚》(“Barn Burning”,1939)以及《村子》的发表,标志着他重拾第三部小说《沙多里斯》中涉及的斯诺普斯家族题材[18],从人物构成和叙事构造上完善了《押沙龙,押沙龙!》所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地理版图。从这个意义上说,斯诺普斯题材焕发了福克纳创作体系的活力。麦卡斯林家族则位于社会阶级之梯的另一极,融合南方白人贵族、原住民和黑人家族的文化动能,合力对抗以斯诺普斯家族为代表的现代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侵蚀。从作家个人生活来看,黑人大妈的去世给福克纳带来巨大影响[19],促使他进一步探索黑人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在后续作品中留有或显或隐的痕迹。另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亦可看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促使美国很多文化人士的左翼倾向发生急转,现代主义文学走向式微。[20]受其影响,福克纳的创作形成了融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体的综合表现手法,或者说他主动超越了单一的现代主义表现形式。
从作品主旨来看,福克纳在他创作生涯的不同时期既遵循了一条主线不变,但前后又有所差异。根据福勒(Doreen Fowler)的观点,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是对人类总体经验的再现,经历了从悲观绝望逐渐过渡到充满希望的过程。[21]在《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中,昆丁·康普生、克里斯默斯和托马斯·萨特潘等主要人物在家族没落、生存困境面前大都束手无策,表现出悲观厌世的情绪。自《去吧,摩西》开始,南方家族的主要成员开始审视历史记忆和遗产传承,另一部小说《大宅》中的明克·斯诺普斯(Mink Snopes)即使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仍然表现出对未来的美好期盼。福克纳后期作品的腔调变得乐观起来。
福克纳对人本身生存境遇的关注是一贯的,只是随着社会环境和生活阅历的变化,个人心态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变而已。1956年初,福克纳在书信中坦承,一年多来感觉“已经江郎才尽,徒有能工巧匠的虚名——对词句再无兴趣、力量和激情”。1961年时他又写道,“三年前就思维干涸了”,“只是以读书为乐,读那些十八岁时就已经发现的旧书”。[22]然而,我们不可由此断定晚年的福克纳灵感枯竭、创作力衰退,因为福克纳的书信和谈话有其特殊的语境。要看到这些言辞多出现于新作出版之前,实际上表露的是作家构思的艰难和焦虑,为自己重复利用素材的做法进行辩解。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词中,福克纳曾经把写作描述为“痛苦而艰辛的事业”,但作家发出的声音理应成为支撑人类社会的“柱石”,帮助人们渡过难关,“走向胜利”。[23]他强调作家在当今社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鼓励年轻作家需不畏困难,始终如一地履行社会交予的使命。在他心目中,作家更好的称呼应为“诗人”,唯有诗才配得上作家的终极遗产。
成为诗人的终极理想也暗示了作家生涯的可持续性。美国叙事学家韦恩·布斯(Wayne C.Booth)注意到了福克纳的后期变化,在普通人看来他是一位关心时事、头戴桂冠的公众人物,而评论家们则更认可那位写作挥洒自如、风格晦涩的意识流小说作家,两个群体均忽视了福克纳作为“事业作家”(career-author)的主观能动性。所谓事业作家,指的是“一系列隐含作者构成的持续性创作中心”,是大多数传记作家和评论家默认的作家。布斯以早、晚期的福克纳为例指出,作家职业的持久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时期隐含作者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布斯认可福克纳后期作品的风格变化,“看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但这种前后变化很难用隐含作者理论进行解释。[24]布斯采用折中观点,承认福克纳写作生涯发生了多次变轨,然而这只能归结于一系列隐含作者之和,即事业作家。换用兰普顿(David Rampton)的话说,福克纳题材、文风和创作动能上的复杂多变给人留下“系列福克纳”(serial Faulkners)的假象。[25]
为便于分析,很多评论家会将作家连续性的写作生涯做出主观划分。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以1950年福克纳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为分界线,如巴塞特编辑的《威廉·福克纳的批评遗产》一书收录1950年8月《短篇故事集》出版之前的有关福克纳诗集、小说和短篇故事集的评论94篇。巴塞特在序言中声明,很多评论集已经收录了战后福克纳研究中涌现出的重要成果,“到1950年他获得诺贝尔奖截止”的做法是“明智”的。[26]巴塞特的暗示有二:一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名”会带来许多夸大其词的宣传报道,二是所收评论对后续福克纳研究的繁荣会起到推动作用。1985年在日本伊豆召开的主题为“诺贝尔奖之后的福克纳”(Faulkner:After the Nobel Prize)国际学术研讨会,直截了当地号召与会专家学者关注1950年以来的后期作品,研判作品的美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至少有三位传记作家将20世纪40年代称为福克纳的“黑暗岁月”。[27]学者们认为,这一时期福克纳的“个人声誉降至低谷”[28],作家对其创作能力产生怀疑,被迫进入一个关键转折期[29]。我国学者肖明翰也指出,《去吧,摩西》出版之后福克纳进入“一生中最长的‘沉默’期”,主要原因在于作家自身和家庭经济状况恶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30]另一位中国学者陶洁的结论与之类似:作家“长期不发表作品”以及写作风格本身晦涩难懂,到40年代中期福克纳的小说“除《圣殿》外已经绝版”。[31]这些论断是对此间福克纳多元化创作经历的认识偏误:作为长子,福克纳正用一支笔杆为稻粱谋,孜孜不倦地创作短篇故事、小说和电影剧本。虽然《烧马棚》和《村子》分别给他带来了欧·亨利短篇故事奖和普利策小说奖,但是福克纳的经济压力并未出现较大程度的缓解。1940年5月他向朋友抱怨:作为一位“真正的、一流的作家”,他却不得不为了全家人的吃喝拉撒、出行、求医乃至妇女卫生用品操心。[32]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品在美国的接受了。1939年萨特在法国挖掘并传播了《喧哗与骚动》的重要价值,而美国国内直到1944年才由考利着手编纂《袖珍福克纳读本》,当时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只有《绿枝》(A Green Bough,1933)和《村子》,难觅其他作品。[33]
任何事情到达谷底就会有反弹,福克纳创作的衰退论即在客观上促成了“福克纳复兴”现象的出现。“福克纳复兴”一说的发起者美国学者施瓦茨(Lawrence H.Schwartz)曾指出:福克纳在40年代的重新崛起并非考利《袖珍福克纳读本》的一己之力、一人之功,而是出版市场上的平装本革命、新批评理论家、纽约知识分子派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不同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34]施瓦茨深入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底蕴,把美国国内的社会语境以及战后冷战思维主导下的文化和外交政策结合起来,在文化研究框架内重新考察福克纳崛起的国内外社会环境。然而,这种完全脱离福克纳文本的外部研究容易给人一种纯思辨的印象。
另一位学者杜瓦尔(John N.Duvall)从20世纪40年代盛行的侦探小说入手,对福克纳相关短篇故事创作的出版环境与读者认知进行分析,发现福克纳借助《埃勒里·奎恩推理杂志》(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走向更广阔的大众阅读市场。福克纳的复兴发生于两条战线:一是考利为代表的精英读者群,另一个是侦探小说畅销的“低俗”市场。[35]杜瓦尔从文类流传的角度考察福克纳的复兴,这一做法值得肯定,但他忽略了两点:侦探小说不仅为作家所钟爱,它的流行与国内外紧张的社会氛围不无关联;所谓“低俗福克纳”形象的出现,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印刷文化现象,因为《圣殿》《野棕榈》《坟墓的闯入者》等小说平装本多次重版,极其畅销。40年代的福克纳为经济状况所困,直到他将《坟墓的闯入者》以高昂的价格转让电影版权之后,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善。
还有学者从作品形式和内容上考察福克纳前后期创作的变化。福克纳的法语翻译家库安德娄(Maurice Edgar Coindreau)在1952年出版的《野棕榈》法语译本序言中指出,《没有被征服的》是一部分水岭式的小说,在此之前作家专注于文本的“形式统一性”,此后则主要“将材料东拼西凑起来”而成为小说。[36]福克纳把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几个短篇故事收集起来,选取某个中心人物作为衔接手段,再加入一篇新作,经过通篇修改之后而成一部新小说。与之相似,斯金弗(Mauri Luisa Skinfill)以《村子》为界,认为福克纳小说的侧重点开始由种族转向阶级。[37]克雷林(Michael Kreyling)继续回溯到《押沙龙,押沙龙!》,指出该作标志着美国南方文学整体上进入后南方(postsouthern)时期。[38]
本书依照斯威加特(Peter Swiggart)的做法,将《去吧,摩西》作为福克纳后期创作的开端。[39]首先,家族人物的形象发生转变,作家抛弃了沙多里斯和康普生家族的荣耀历史,而是转向对祖、父辈的缺点和痛点进行批判。虽然《押沙龙,押沙龙!》已经开始批判萨特潘的重婚与遗弃妻儿经历,父辈过错在《去吧,摩西》中演变为祖辈的父女乱伦,对父辈功德的歌颂扭转为对他们的揭批审判。其次,《去吧,摩西》之后的多部作品以时间跨度见长,从密西西比边疆开拓的18世纪,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五十年代,作家的历史视野更为开阔,对历史题材的驾驭更加娴熟。再次,小说人物众多、关系繁杂,故事情节在人物之间的联姻、乱伦、蓄奴等活动中得以推进、拓展或逆转。南方的比彻姆、埃德蒙兹、法泽斯、普利斯特等在不同作品中融入麦卡斯林跨种族、跨阶级的家族版图,后期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坟墓的闯入者》《大森林》《掠夺者》可谓《去吧,摩西》的续作。因此,这部小说作为福克纳后期创作的扛鼎之作,深入探讨其中的家族主题对于后期作品研究可以起到提纲挈领之效。
学界对福克纳后期作品的看法,总体而言较为负面。美国学者辛格尔(Daniel J.Singal)语带偏激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福克纳生命后二十年的创作数量和质量均“急剧下降”,前后期作品质量简直判若云泥。[40]1929—1942年的创作高峰期过后,福克纳的写作和出版速度有所放缓,但辛格尔之见显然过于绝对了。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授兰普顿就福克纳一生写出的小说总量(共19部)得出了更为客观的结论:比起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伍尔夫等同时代作家,福克纳真的“非比寻常”。[41]持续而稳定的文学产出有力回击了评论界有关福克纳创作力的断层论与衰退说。
衰退说的副产品是学界对前后期关注度的不均衡现象,[42]后期作品的研究也多围绕斯诺普斯三部曲展开。其实,斯诺普斯家族故事贯穿于福克纳文学生涯始终。对这个白手起家的穷白人家族,福克纳早在《沙多里斯》中即将其作为名门望族的对立面有过不少描述,后来的《村子》集中展示了弗莱姆对金钱的贪婪,但真正全面讲述这一家族历史变迁的是在《小镇》和《大宅》中。在学术史上,最早以三部曲的形式进行考察的是贝克(Warren Beck)1961年出版的专著《变迁中的人:福克纳的三部曲》(Man in Motion:Faulkner’s Trilogy),该作重在分析三部小说各自的结构,区分不同的叙述模式,指出相互之间在故事内容上的关联。贝克探讨主要人物形象,阐述了福克纳使用的反讽和怪诞手法,强调作家着力表现人与社会的变迁这一核心主题。1968年,华生(James Gray Watson)出版了第二部斯诺普斯三部曲研究专著《斯诺普斯困境:福克纳的三部曲》(The Snopes Dilemma:Faulkner’s Trilogy),正式提出“斯诺普斯主义”的概念,华生认为弗莱姆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所有非道德的一面,斯诺普斯家族成员始终处于道德认同与非道德的“斯诺普斯困境”之中。[43]
后期作品研究的真正转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在巴黎大学召开的首届国际福克纳专题研讨会上,传记作家布洛特纳(Joseph Blotner)考察了福克纳的生平与创作生涯之后指出,作家“最后十五年”的生命经历“暗示了改善人类境况的某些方面的可能性”,这期间他的经济状况改善,在公众场合中频频发声,与妻子的关系也逐渐好转,这些因素使得后期作品增添了“某种积极的腔调”,但这种积极态度与前期作品中的悲剧色彩一脉相承,或者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44]1982年4月,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福克纳专题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大桥健三郎(Kenzaburo Ohashi)撰文指出,福克纳作品体系中存有一张“动态”的互文性网络,在很多学者看来后期作品出现的重复现象其实是“自我戏仿”。福克纳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并未止步,而是对前期作品进行总结、修正与革新,希望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续自己的创作生涯。[45]这一观点为学界重新评估福克纳的后期作品带来新动力,直接促成了三年后在日本伊豆(Izu)召开的主题为“诺贝尔奖之后的福克纳”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更多的专家学者专注于探讨福克纳后期作品,研判它们的美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瑞典学者汉斯·斯凯(Hans H.Skei)。他赞同福克纳小说体系具有“内在延续性”的说法,注意到福克纳前期作品中出现的某些人物、事件、主题和题材后来被作家重复使用,认为此类重复实际上暗含了深层次的变化和革新,这反映了作家对人及其能力“更平衡、更热情的理解”,赋予作品新的时代意义。[46]在一年一度的“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上,1992年和2000年两届年会由普尔克(Noel Polk)和唐娜(Theresa M.Towner)分别撰文,呼吁学界对福克纳的后期创作加强研究、进行重估。
80年代末开始,美国学界出现了以福克纳后期部分小说为研究对象的专著。1989年美国出版了两部。乌尔果(Joseph R.Urgo)的《福克纳的伪经〈寓言〉斯诺普斯与人类反叛精神》(Faulkner’s Apocrypha:“A Fable”,Snopes,and the Spirit of Human Rebellion)一书首次提出:后期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前期小说,是对前期小说的超越;以斯诺普斯为代表,福克纳为世界文学留下了不朽的反叛者形象。乌尔果对学界鲜有问津的小说《寓言》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另一部专著来自曾达(Karl F.Zender),他的《道路的交叠:威廉·福克纳、南方与现代世界》(The Crossing of the Ways:William Faulkner,the South,and the Modern World)中大部分章节均围绕四五十年代的小说展开论述。2000年唐娜出版的《福克纳后期小说中的种族差异》(Faulkner on the Color Line:The Later Novels),旗帜鲜明地指出:福克纳并非普通读者和大部分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将小说视作发表个人政见的平台,而是在1950年之后的作品中刻意展现了作为公众人物对立面的形象,作家甚至对自己的种族意识发出质疑。拉巴特(Blair Labatt)的《讲故事的福克纳》(Faulkner the Storyteller,2005)围绕部分短篇故事和斯诺普斯三部曲对福克纳的叙述技巧亦进行了重点探察。
学术史上三部早期文献奠定了福克纳创作题材与宏旨一贯性的基础。在哈古德看来,福克纳研究进入“成熟期”之后,作家每发表一部作品,都会在“更大的文学圈子内部”形成对话,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奥唐奈(George Marion O’ Donnell)于1939年发表的《福克纳的神话》(“Faulkner’s Mythology”)一文。这篇文章开启了福克纳研究中的“南方神话”范式,聚焦作品中传统与反传统势力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以沙多里斯和斯诺普斯为代表的两派势力的较量。奥唐奈之后的里程碑文献是考利的《袖珍福克纳读本》,哈古德称之为“力挽狂澜”之作,也是福克纳批评大规模出现的“真正火种”。[47]考利在序言中强调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整体性,推进了奥唐奈发起的南方范式。这本星火燎原之作的副产品是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刊发于《新共和》的书评《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作为新批评学派的重要一员,沃伦基于文本细读,把福克纳的南方小说阐释为有关现代人共有“苦难和疑难问题”的传奇。[48]不容忽视的是,此类评论的出现与作家本人的创作形成了对话,比如福克纳曾就考利早期发表的文章回信,对个中观点表示肯定。[49]这样的对话客观上推进了福克纳书写“人类内心冲突”(语出诺贝尔受奖演说)的伟业,确保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福克纳后期文学创作生涯的高光时刻,对于他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意味着新的开始。1949年可能获奖的消息传来时,福克纳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宁愿与德莱塞和舍伍德·安德森待在同一个鸽子洞”,而不屑与已经获此殊荣的辛克莱·刘易斯和赛珍珠为伍。[50]福克纳就是如此矛盾的个体,大半生的文学积累已经令其名垂美国与世界文学史,可依然不为名誉所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写作事业。这份坚守就像他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南方人物,上至先祖下至玄孙,正是得力于作家持之以恒的创作力,才不断延续着他们的生命,从一部小说游走至下一部。福克纳的后期小说不少是回溯性的,从时间上看形成一个闭环,比如收山之作《掠夺者》以“祖父讲述道”开篇,回忆的是1905年发生的事情,这一时间点是《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小说屡次描绘、对人物至关重要的。从故事时间上看,人物的过去“并未过去”,另从美国文学的传承来看,叙事传统在福克纳这里并未断裂,且开创了未来。同为美国南方作家的奥康纳(Flannery O’ Connor)如此描述福克纳对当代作家的深远影响:“我们中间出了一个福克纳,真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影响到了作家能力内外的方方面面。没人想把自己的车马驶入‘迪克西有限公司号专车’呼啸而过的车辙!”[51]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福克纳的创作一直没有离开家族题材,不愧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家族小说家”[52]。英语中的family一词用于指涉人的血缘关系与成长环境时,兼有汉语中的“家庭”和“家族”两层含义。一般意义上,家庭指的是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构成的核心家庭(nucleus family),主要涉及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时间线一旦延长,父母拥有自己的父母,子女将来也会成为父母,因此家庭“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这种“绵续性”使家庭历史化为家族。[53]可见,家族强调血缘或者亲属关系,可看作家庭的历史化和社会化。家族已经涵盖,但会大大超出核心家庭中的亲子关系,转而强调成员间的价值观传承与心灵归属。
家族成员之间纵向结构的“绵续性”要求至少三代亲属、两个时序上有先后且存在时间重叠的核心家庭构成,两个家庭聚合主要根据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的达成是亲子关系形成的前提,两个时间上大致平行存在的核心家庭构成横向的婚姻关系。家族成员之间在血缘和婚姻关系上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当然,家族关系网络中的某位家族成员可能因意外或疾病夭折,成年后因婚前、婚外性关系甚至乱伦而拥有私生子女,父母缺乏生育能力而收养无血缘关系的子女,诸种情况都会增加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更广义上说,家族还应包括堂兄弟姐妹,乃至任何可以追宗溯祖的同一姓氏成员。
国内外福克纳学者一般不再区分家庭和家族这两个概念,但具体研究的侧重点会有不同。比如,约翰逊(Claudia Durst Johnson)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结合社会学理论对小说中的家庭主题进行解读。[54]另一位学者金尼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按照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不同家族进行归类,陆续编辑出版了四卷本“威廉·福克纳批评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William Faulkner:The Compson Family(1982);The Sartoris Family(1985);The McCaslin Family(1990);The Sutpen Family(1996)]。我国福克纳研究的开拓者肖明翰,在《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1994)一书中首次明确了福克纳小说中的家族变迁主题,并与巴金小说进行对比研究。略有遗憾的是,该著作副标题中出现的“家庭小说”一语不能涵盖全书的主要内容,主副标题之间有抵牾之处。武月明《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2013)和李杨《颠覆·开放·与时俱进:美国后南方的小说纵横论》(2018)两部著作均将family直译为“家庭”,无法与福克纳的家族题材形成密切对应。
在福克纳学术史上,除了family,不同学者还运用了clan和saga等词指代家族。纽约知识分子派文学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明确指出:家族(clan)构成了福克纳小说世界的“基本社会单位”,“家族荣耀”和“祖先崇敬”是小说中南方贵族人物行事处世的“强大动因”。例如,《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家族第四代长子昆丁引以为豪的是,祖上出过一位州长和三个将军,家族荣耀的记忆令他沉溺于家族历史的光环,无法接纳当前经济状况恶化和家人道德堕落的现实,最终被迫选择投水自尽。相比之下,弟弟杰生几乎抛弃了全部家族传统,追逐金钱利益的最大化,逐步将全家推向分崩离析的深渊。正是通过对家族败裂的描绘,福克纳记述了“传统南方社会的衰朽”。[55]欧文·豪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分解为各有特色的家族群体,确立了福克纳小说批评的基本单位,突破了奥唐奈1939年以来倡导的贵族与穷白人阶级对立为核心的批评传统,将重心转向基于人物行为习惯和家族门第的道德批评。另有两位学者(Chabrier Gwendolyn,1993;Stephens,1995)借用北欧“萨迦”(saga)这一特殊的文类指代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家族小说。
福克纳本人曾在后期小说《大宅》中同时使用四个术语指代家族的概念,以达到强化血肉联系的目的。叙述者是斯诺普斯家族的一个成员蒙哥马利(Montgomery Snopes),他对全族做出一番讽刺性极强的评判:
我来自于你所谓的一个家族(family)、宗族(clan)、种族(race),甚至可能是物种(species),我们都是狗崽子(sons of bitches)。我才会说,好好,要是事实真的如此,我们会露出马脚的。人们会把最好的律师称为律师中的律师,称最好的演员为演员中的演员,称最佳球员为球员中的球员。那么,我们也会说:每个斯诺普斯都会将其视作个人目标,要让全世界认识到,他就是狗崽子中的狗崽子。[56]
蒙哥马利使用一个脏词“狗崽子”表达了个人对家族背景的憎恶,这种负面情感表现于两方面。一方面,从字面上看,“狗崽子”一说是对女性长辈的诅咒,是颇具厌女症倾向的心理外化;另一方面,人物强调斯诺普斯家族成员从事行业的多样性,但评判标准只落脚于道德品行,基本否定了这一家族内部缺失的凝聚力。因此,对于大部分斯诺普斯成员而言,家族关系网是急于逃脱的囹圄。
放眼世界文学史,人物的家族关系是19世纪以来家族题材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当时,欧洲文坛兴起了书写显赫贵族的热潮,如法国的左拉(Emile Zola,1840—1902)在1871—1893年陆续出版的《鲁贡-马卡尔家族史》(Les Rougon-Macquart)系列小说多达二十部,著名的《娜娜》(Nana,1880)和《萌芽》(Germinal,1885)便位列其中。到了世纪之交,英国小说家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的“威塞克斯”(Wessex)系列小说已经蔚为大观,其他英国小说家也在运用类似手法创作有关社区及其历史变迁的文学作品。在此背景之下,地方性编年史(provincial chronicle)作为一种新形势下的“萨迦”应运而生,代表作有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的《克雷函》(Clayhanger,1910)、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的《虹》(The Rainbow,1915)以及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The Forsyte Saga,1906—1921)。这些文学作品强调人物所处地理与人文环境的重要性,突出家族的时间跨度,显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的生存困境,以厚重的历史意识彰显小说这一文类独特的承载力。[57]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家族文学的创作动能得以延续。除了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典型的家族小说还包括德国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1919)、法国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1881—1958)的《蒂博一家》(Les Thilbault,1922—1940)以及林语堂在美国以英语出版的《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1939)。福克纳是此类小说的忠实读者,对《布登勃洛克一家》情有独钟,在1940年一次访谈中称其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58]。鉴于家族主题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的受欢迎程度,法国文学家和评论家们将其归入一个特殊的类别,称其为长河小说(法语roman-fleuve),专用于指代那些描写单个或多个家族的生活场景与家族关系,“从形式到内容具有大江大河般气势”的多卷本小说。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的《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1912)属滥觞之作,该书序言指出:“每个生命的方式是自然界一种力的方式”,“我觉得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条河”。[59]
长河小说并非欧洲专属,美国文学中的家族主题及相关文类也由来已久。19世纪中期,女性小说家们的主要阵地是“家庭小说”(domestic novel)。当时,美国文坛涌现出了诸如索思沃斯(E.D.E.N.Southsworth,1819—1899)、沃纳(Susan Warner,1819—1885)、弗恩(Fanny Fern,1811—1872)、威尔逊(Augusta Jane Evans Wilson,1838—1909)和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等著名女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家庭是一块“由男性主宰,但又被社会界定为女性特有的领域”,女性作家本着“对于女性地位与命运的深切关注”,塑造出“具有传统价值观的玛利亚式的女性形象与富有夏娃式独立精神的女性精神相结合的文学形象”,她们“身负重担,既是称职的家庭妇女,也能在男性统治的传统社会领域里大显身手”。[60]这些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不乏乌托邦色彩,寄托了“重建母性帝国”的社会理想,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她们大多需要依赖男性慈善家提供“物质基础”。[61]女性作家关注的焦点在于女性人物的生活境遇与社会理想,她们的崛起恰逢霍桑(Nathanial Hawthorne,1804—1864)的罗曼史(romance)诗学兴起,而后者小说中浓重的家族历史意识与女作家们的家庭小说形成互补。两者合流,与南方种植园小说中的家族传统相呼应。这种家族传统在19世纪末期以来的小说中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南方文艺复兴前后,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1873—1945)的《战场》(The Battle-Ground,1902)、海尔曼(Lillian Hellman,1905—1984)的《小狐狸》(The Little Foxes,1939)和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的《三角洲婚礼》(Delta Wedding,1946)都是这方面的佳作。
家族传统与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主题、历史意识和地方文化密切相关。美国罗格斯大学的托宾(Patricia Drechsel Tobin)将小说叙事的线性流程与家族小说中的代际传承结合起来,两者的关联即为“家谱约束”:“通过功能上的类比,时间中的事件类似于家谱的序列线程,能够根据因果线程而孕育出其他事件,时序在前的事件会赢得格外的关照,会给人以生发、控制和预测将来事件的感觉。当本体论上的优先性以如此方式归置于单纯的时间先在性,历史意识就会诞生,时间就可理解为一种对家谱式事件归宿的线性呈现。”[62]与之相似,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威尔吉(Jobst Welge)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家族与政治身份的辩证关系,将19世纪以来以家族衰落为主线的小说划归为家谱小说,认为名门望族的衰落轨迹象征他们不甘退居社会边缘的文化心理。虽然威尔吉选取的文本并不包含福克纳的小说,他对拉美地区西班牙、葡萄牙语作家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出福克纳在个体记忆的塑造和意识流叙事技巧方面对后世作家的深层次影响。[63]换句话说,福克纳的家族小说给拉美作家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家族的地缘性不容忽略。福克纳小说中的南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问题。根据盖洛普的定义,美国南方指的是内战前组成邦联的弗吉尼亚、佛罗里达、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田纳西、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西西比、得克萨斯、肯塔基和俄克拉何马共计13个州。[64]地理意义上的南方是十分宽泛的,然而对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而言,南方代表了人们对家乡和地域的“认知方式”[65],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已经内化于日常语言和文艺作品中。自新批评理论家的阐释开始,南方在福克纳笔下表现为约克纳帕塔法,进而缩影着全人类的象征体。
传统文学作品和流行文化中,南方的标志性符号一直是黑奴、棉花田、种植园等司空见惯的人物形象和自然景物,这些几乎成为经济落后、暴力犯罪频发、社会地位不高的代名词,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南方的文学形象。1917年,《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Mail)登载了著名评论家门肯(H.L.Mencken,1880—1956)的一篇名为《艺术的撒哈拉沙漠》(“The Sahara of the Bozart”)的文章,认为整个南方文学在经历了19世纪后期的短暂繁荣之后,回归至一片荒原般景象,“艺术、思想和文化上有如撒哈拉沙漠一样贫瘠”。或许他的判断带着地区偏见——“欧洲一英亩土地上就能找得出波托马克河以南所有州里同等数量的一流人士”,门肯只是抒发对当时南方文化现实的不满,持有怀旧的眼光看待现状——除了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1879—1958),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位南方小说家。[66]这样的观点未免显得激进,实际情况是美国文学分布极不均衡。有研究者指出,美国文学经历了几十年的新英格兰地区超验主义繁荣之后,1860—1900年美国并未出现特定的“文学中心”。随着20世纪20年代重农派(the Agrarians)的出现,文学的中心渐趋偏向了南方,出现了相当繁荣的景象。[67]也就是说,门肯的批判正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被推翻,“南方文艺复兴”汹涌而来。
美国南方历史学家理查德·金(Richard H.King)详述了南方文学在20世纪中叶前后的极大繁荣景象。金围绕美国南方的家族文化传统,指出“南方可以看作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庞大家族,以血缘关系连结为有机整体”[68]。他注重历史意识的发掘,详细考察南方文艺复兴作家群之后认为,家族罗曼史(family romance)作为一种集体想象,属于美国南方文学的核心题材,集中反映了当地民众的情感结构。金总结了前期福克纳研究中家族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路径,重点阐述了《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小说中父子、兄弟姐妹之间的复杂情感。他还涉及了不同代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亲子关系叠加了家族历史的维度。
与金的研究思路相似,斯蒂芬斯(Robert O.Stephens)以南方文学中的家族小说发展脉络为主线,重点考察了家族世系的典型特征与代表作品。他深入研讨了福克纳的两部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斯蒂芬斯认为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再造了历史学家型叙述者(narrator-historian),运用限知视角取代传统家族世系小说中的全知视角,留给小说人物以及故事外的读者“故事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印象。同时,作家充分阐发了“社区是家族的延伸”这一观念,任由康普生家族的后辈在约克纳帕塔法的社会语境中重构自己的家族史,强化南方社区的内聚力与封闭性。[69]《去吧,摩西》则做出了家族世系的另一种创新,作家弃用线性叙事模式,转向以长短不一的故事片段客观呈现家族编年史,突出人物家族记忆的重要性。斯蒂芬斯指出,福克纳的这种叙事手法可能模仿了旧约《创世记》的编纂方法——把单个故事拼接起来,置入新的上下文,实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艺术效果。
形式研究之外,福克纳小说中的家族主题更受关注。作家在安德森的点拨下正式将乡土人情纳入文学创作之后,深掘南方白人家族的历史渊源与兴衰轨迹,在《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三部代表作中细致刻画了各家族的家谱结构和代际源流。这些作品成为福克纳小说家族研究的主要拥趸——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金尼教授的关键研究对象。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四卷本《威廉·福克纳批评论集》,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四大南方贵族世系为单位,对福克纳小说中的家族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汇总。该系列的编纂体例相同,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作者个人观点、当代评论与接受以及学术史上的经典批评文献。它的一大特色是突破单一小说文本乃至文类的局限,从福克纳作品的整体性出发,选取各家族相关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如《康普生家族》涵盖了《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附录》《夕阳》等不同文本。作为对整套书系的概括,金尼全面介绍了四大家族的基本脉络,点明了福克纳在不同家族书写中各自的着力点:沙多里斯家族的荣耀感,康普生家族的衰败,萨特潘家族的宏大规划以及麦卡斯林家族深藏的人伦罪恶。[70]
不同于金尼的家族列传模式,另一位学者查布里尔(Gwendolyn Chabrier)则从地域文化、女性形象、亲子关系以及乱伦、混血和收养等问题入手,系统阐述福克纳的主要家族罗曼史及其反映的社会问题。查布里尔认为家族记忆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物的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关福克纳的家族世系小说,查布里尔发现前后期作品的总体基调存有差异,后期写作剔除了“夸大南方家族负面形象”的做法。[71]在南方家族暴露的社会问题方面,查布里尔注重考察家族成员对后世及周围人物的多重影响,一旦个体出现问题,家族(至少在两代人的家庭内部)就可能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查布里尔对南方家族文化的阐释较为深刻,但似乎过于依赖福克纳的个人经历,推导文学创作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这种社会学研究范式容易忽略福克纳作品的虚构性。
还有一位学者里孚(Mark Leaf)倡导破除福克纳研究中的贵族与穷白人家族二元对立。他以斯诺普斯三部曲为例指出,学界通常将弗莱姆·斯诺普斯与沙多里斯、麦卡斯林等传统的白人贵族截然对立,前者从两手空空到新晋权贵的发迹史冲蚀了南方传统贵族的经济与道德根基,这样的看法主要基于《我弥留之际》《花斑马》《没有被征服的》等前期作品。其实,在福克纳长期的写作生涯中,主导手法出现了从象征到写实的过渡。里孚援引考利的评论进一步指出,福克纳对早期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形象逐渐流露出一定的矛盾乃至怜悯的情感,弗莱姆“最后获得了一种补救性的尊严感”。因此,里孚强调研究者不但要关注文本中发生的事件,更要注重分析叙述者自身“含蓄流露出来的对诸事件的心态”。换句话说,叙述者虽然并未讲述个人经历,但讲述行为本身掺杂了他们对事物和事件的看法,不可避免地传达出各自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这些正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最后,里孚直截了当地指出,“小说文本复杂的叙事结构即是叙述者形象的外化”[72]。
以家庭为母题的福克纳研究中,传统的做法是遵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如欧温(John T. Irving)认为人物的自恋源自兄妹乱伦的欲望,而这又是母子乱伦的替代品。[73]斯托霍夫(Gary Storhoff)则从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入手,不仅研究个体心理,而且关注外部环境以及家庭其他成员施加的影响,为福克纳家族小说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74]华生从优生学的视角分析福克纳早期小说《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中的白人家庭,发现福克纳早年的北方游历与美国开展的优生学运动南下形成一个交集区,作家对南方白人问题家庭及其成员关注度提高。[75]这种借助优生学话语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昭示了文学批评的边界在文化研究影响下持续外溢,忽视了文学作品内在文学性的重要价值。
巴塞特(John Earl Bassett)在80年代陆续发表的三篇论文,系统探讨了福克纳小说中的家族主题,后来收入1989年出版的《视野与修订:福克纳散论》(Vision and Revisions:Essays on Faulkner)一书。论及《沙多里斯》时巴塞特认为,这是一部“一分为二”的小说,前两部分主要围绕老贝亚德和孙子的价值观念冲突展开,从第三部分开始福克纳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小贝亚德和本鲍的关系,转向沙多里斯和本鲍两大家族的既有冲突。关于《喧哗与骚动》,巴塞特采取传记与文本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福克纳童年时期感受到的兄弟竞争以及来自母亲的偏袒与冷漠,探讨康普生家四子女之间的感情经历,强调父母在子女心灵成长过程中的影响。在关于《我弥留之际》的分析中,巴塞特继续以传记研究的思路考察本德仑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与矛盾。
法国学者格里赛(Michel Gresset)考察了福克纳的《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标塔》《押沙龙,押沙龙!》《野棕榈》等前期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发现家与性或欲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指出家的观念对男性人物而言并无固定内涵,而是一种表达异化和怀旧的手段。这些人物成为福克纳塑造的一个庞大的无家可归群体,如霍拉斯·本鲍(《沙多里斯》和《圣殿》)、康普生三兄弟(《喧哗与骚动》)、乔·克里斯默斯(《八月之光》)、亨利·萨特潘(《押沙龙,押沙龙!》)等重要人物形象。相比之下,有的女性人物则可以等同于家本身,如艾迪·本德仑(《我弥留之际》);而凯蒂·康普生(《喧哗与骚动》)和夏洛特·里滕迈耶(《野棕榈》)根本不关心肩负的责任与义务,为家人造成无家可归之感。格里赛进一步指出,福克纳之所以如此深入挖掘人物的无家感,是因为他个人的深重孤独感,在自己家中也仅是忙于创作而“无家可归”的人。[76]该文将人物分析与作家生活结合起来,总的来说属于传记式批评,格里赛有关男、女性人物对家的不同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物身份的形成机制。
另一位学者鲍姆(Rosalie Murphy Baum)同样聚焦于家庭问题,她指出,福克纳的小说可以看作“家庭内部暴力与虐待的汇编”[77]。她根据社会学研究的相关理据与分析方法,按照施暴对象的不同将福克纳小说中的家庭暴力对象分为夫妻和子女两大类,具体形式又分为身体暴力和情感暴力两种,而儿童遭受的家庭暴力受到作家的特殊关注。在鲍姆看来,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不利于儿童成长,但也存在成人施暴者本身就曾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情形,这就造成家族内部情感缺失甚至虐待不止的恶性循环。
波特(Carolyn Porter)亦指出,福克纳主要小说中的家庭题材赋予性别关系重要的主题意义,家不仅仅是“个体内心矛盾冲突的原发场地”,还作为一种中心性社会结构激发和囊括了人物内心冲突。在福克纳前期作品中,作者的性别关注重心发生或隐或显的转移——由以《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母亲为中心过渡到以《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的父亲为中心。随着重心的偏移,福克纳的故事背景也从聚焦于核心家庭慢慢拓展到了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家族叙事。[78]
相较于格里赛、鲍姆和波特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关注,埃利斯特(Mark Allister)将关注点转向小说中的建筑实体及其折射的个人心理。他重点分析了建筑与个人雄心的关系,以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托马斯·萨特潘的个人与家族经历为中心,分析福克纳的家族世系小说。[79]埃利斯特发现,萨特潘庄园的短期内崛起也预示了家族命运的快速败落。福克纳对南方贵族的刻画以《押沙龙,押沙龙!》为分水岭,庄园建筑在1936年之后出版的小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庄园主的宏大设计即是从这些庄严宏伟的建筑上体现出来的。在埃利斯特看来,萨特潘的个人与家族浮沉在福克纳作品中具有典型性。正如他对萨特潘的批评——与将物质生活的外在形式与道德品行的内在本质相混淆一样,埃利斯特过于强调建筑在福克纳家族叙事中的重要性,疏于对种族和阶级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挖掘。
美国传记作家布洛特纳曾撰文对福克纳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进行考证,认为作家通过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改头换面,塑造出一大批明显高于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性格中的冒险、流浪乃至粗俗之处。[80]这类研究带有明显的传记式批评痕迹,侧重于考证文本内外人物的异同性,对作品文学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如作家本人所言,纵观福克纳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其实他是在书写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传记作家从作家到作品的思路难以避免,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主义大潮兴起之前。另一位传记作家敏特(David Minter)亦指出,福克纳基于自己优厚的家族背景,在创作中特别关注人类遗传的重要性,重视对家族传承的描写。[81]
福克纳学术史涌现出不少研究家族关系或个别家庭成员形象的著述,亲子关系受到的关注最多。福勒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角度探讨福克纳塑造的父亲和代理父亲(surrogate father)形象,但不同于俄狄浦斯情结中的父子对立关系,福勒转向父亲形象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的弥合矛盾与分歧的作用,例如《坟墓的闯入者》中律师加文和黑人卢卡斯作为主人公契克的代理父亲功能。[82]母亲形象研究的代表作是克拉克(Deborah Clarke)的《抢劫母亲:福克纳作品中的女性》(Robbing the Mother:Women in Faulkner,1994),作者从女性主义立场分析女性身体和男权影响,重点围绕母性展开对母女关系的探讨。研究发现,福克纳的女性人物借助母亲生殖力的隐喻,模糊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以语言为载体实现母女关系的巩固。[83]
儿童形象方面,普尔克沿用弗洛伊德理论,着重探究前期作品中“大宅深院中囚徒”般的儿童形象。[84]在兄弟姐妹关系的研究方面,欧温(John Irving)的《双生与乱伦》(Doubling and Incest/Repetition and Revenge,1975)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突破新批评模式的论著”[85],该著作运用弗洛伊德和尼采的理论观点,对《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和妹妹乱伦意识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卢瓦肖(Valérie Loichot)从广义的南方——美国南方以及拉美的前种植园殖民地国家——的视角考察了种植园奴隶制对奴隶家庭的深重迫害,认为子女的家庭纽带和个人历史在文本再现中被任意切断,成为双重意义上的“孤儿”。奴隶的家庭悲剧一方面表现为现实意义上的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另一方面是故事中奴隶的家庭纽带被删除,或者量化为经济价值来体现。然而,孤儿们大多会“积极进行家庭重构”,以期建立“虚构的亲属关系”(fictive kinships),“孤儿叙事”更重要的表现为“由孤儿发起”的叙述。[86]分析《八月之光》时,卢瓦肖利用格利桑(Edouard Glissant)的返祖社会(atavistic society)和克里奥尔化(créolisation)观点,探察克里斯默斯的混血身份对美国南方返祖社会的威胁性,福克纳由此开始探索南方转向混合型社会(composite society)。卢瓦肖认为,克里斯默斯的悲剧源于孤儿身份造成的家族无着感。
在中外文化史上,以家喻国、家国天下的观念较为普遍,家族文学研究中通行从家族到国家的研究范式,以家族的变迁影射国家的变革,研究重点落脚于社会整体,将文学再现的直接对象——家族隐喻化。新文化史运动的主将亨特(Lynn Hunt)详细分析了法国文化中视国如家、以君为父的思想,通过发掘法国历史上家族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介入“政治的家庭模型”的探讨。[87]他在保留家族罗曼史横向的社会维度的同时,强调其历史性与政治性,为我们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文学作品不同的家族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范例。
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部福克纳研究的经典之作,即桑德奎斯特(Eric J.Sundquist)的《福克纳——破裂之屋》(Faulkner:The House Divided,1985)。该书援引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总统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著名判断“破裂之屋难持久”(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在历史与政治语境中解读福克纳创作的六部小说《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88]桑德奎斯特综合分析了各小说的结构特征以及种族主题的复杂性,颇有创见性地指出:后三部小说在深化主题的同时,加深了前三部小说叙事形式的意义与价值,使得作品更具思想的深度。这部专著在隐喻层面上拉近了家族与南方社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文学形式与内容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我国福克纳研究中对家庭主题的关注较多。陶洁秉持家庭反映社会生活的理念,重点分析了《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这两部小说,认为以康普生的家道中落、本德仑的经济破产作为美国旧南方分崩离析的表征,作家的婚姻家庭观念较为悲观,部分家庭成员的苦熬精神得到突出和赞扬。陶洁将家庭视作“社会和地区的缩影”[89]。康普生家族的败落着重体现于以杰生三世为首的家长失职,造成昆丁、凯蒂、杰生和班吉四个子女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父爱缺失,母爱仅间接地来自老黑奴迪尔西和凯蒂本人。小昆丁“在没有爱怜的环境中长大而变得性格扭曲”[90],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成员沉溺于过往的家族荣耀,而忽略了人之常情,南方贵族死守家族记忆而无法施爱。《我弥留之际》中普通的穷白人家庭则因各自私欲的膨胀而心怀鬼胎,无论父亲还是子女均无法“享受家庭的温暖”[91]。陶洁指出该小说从正面反映了南方经济的变化,赤贫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扭曲。康普生和本德仑两个家庭“虽然以南方为背景,实际却超越了地区局限”[92]而具有普遍性。总的来看,陶洁遵循的是“家庭隐喻社会”的批评路线。
武月明的《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一书以我国文学批评界独具特色的文学伦理学为主要方法,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将福克纳小说中的种族、家庭、性别、生态等社会问题整合为伦理问题,挖掘作家对人性拷问的伦理学意义。在着重探讨家庭伦理的第四章,武月明从美国南方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家庭问题出发,基于理查德·金对“南方家族罗曼史”的论断,重点围绕《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等小说,探讨人物因父母之爱缺失而造成的血缘关系冷漠,展示家庭成员之间疏离、迷失、阋墙乃至乱伦等亲情缺失的症候。[93]
国内对福克纳家族小说的研究侧重于传统贵族。兰州大学的高红霞以福克纳的家族小说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成果。首先,她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角度切入福克纳家族小说,认为福克纳从内容到形式上深刻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家族小说创作,[94]后来又针对“寻父—审父”母题[95]和《去吧,摩西》[96]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她的另一篇文章[97]在家族、历史和地域的三位一体中考察福克纳家族小说中的失乐园、审父、乱伦和厌女等四大母题,以族谱为中心挖掘福克纳历史意识的内在矛盾性及其对美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该文是目前为止国内福克纳家族小说研究的最重要成果。综合可见,高红霞的关注点集中于南方白人贵族家庭,并未涉及1942年以后出版的其他家族小说,更多地着墨于小说的主题意义而非文学形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近年陆续出现了集中探讨斯诺普斯家族的研究成果,如曾军山、黄秀国、谌晓明和韩启群分别从解构、互文性、物质文化等角度探讨斯诺普斯三部曲的文本呈现与社会意义。[98]
聚焦家族主题的研究成果集中发生于比较文学领域。韩海燕较早把福克纳与中国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发现毁灭和家族是曹雪芹和福克纳共同关注的概念,韩海燕依托家族衰落的主题,进一步比较了两位作家塑造的多个女性人物形象。[99]她强调人物性格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女性人物天性的自然宣泄大多会遭到外部势力的打压,人物性格冲突又加剧了家族的衰落。韩海燕一文侧重于人物个体与家族集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未深入两国相异的文化价值观层面,也没有探讨福克纳和曹雪芹的写作手法。
随着福克纳译介的深入,肖明翰推出了国内首部将福克纳与中国现代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他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框架之内,着力探讨两位作家创作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对家族问题的极大关注。[100]肖明翰从家庭和宅邸、家长形象、青年一代、女性人物以及奴仆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两作家创作的家族小说异同,还详细分析了两人在写作手法上的差异。该作以人道主义关怀为主线,将“大家族的没落”轨迹视作社会变革与转型的预言,发现伟大作家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作家思想及作品均为当时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产物。[101]应该看到,该作将两位作家置于平等的位置上,并不单纯强调影响,不区分出伯仲,这种研究姿态可能也与福克纳和巴金(1904—2005)的年龄相近有关。
21世纪以来,比较文学领域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朱宾忠《跨越时空的对话: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2006)和李萌羽《多维视野中的沈从文和福克纳小说》(2009)两部著作拓展了可比作家的选取范围,从主题兼形式的角度进行综合对比。张之帆的《莫言与福克纳——“高密东北乡”与“约克纳帕塔法”谱系研究》(2016)将两作家的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她对朱宾忠一书流露出的莫言不及福克纳的观点——师徒关系——进行了纠偏,循着肖明翰的研究思路将中美两国的作家平等对待,以家族为切入点进行平行研究,重点从家族、土地和信仰三方面对家族谱系东西方差异的根源进行研究。张之帆抽取结构人类学中有关地缘与血缘构成不同社会组织方式的观点,对莫言和福克纳小说中的家族谱系进行了细分,离析出作品中惯常出现的“祖—父—我—子”[102]四代家族结构,使得人物的家族关系更加明晰。但是,这部著作对结构人类学部分观点的理解比较片面且机械,没有联系结构主义诗学、心理分析等相关学派的观点,对文学作品形式背后的主题意义深入分析。
由上述对国内外学术史和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福克纳后期作品逐渐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已经摆脱重前期、轻后期的趋向,开始发掘斯诺普斯三部曲和其他后期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有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首先,后期作品研究的目标对象比较单一,无论在叙事形式还是主题研究上,并未出现整体性的深入研究成果。以挪威学者斯凯为代表的短篇故事研究者们,刻意从文类角度强调福克纳取得的重要成就,呼吁学界对短篇故事及其在后期小说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展研究。另有部分学者[103]专以斯诺普斯三部曲为对象,从不同视角分析该平民家族罗曼史在福克纳家族小说中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然而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出现了跨媒介势头,1942年后福克纳介入小说、电影、戏剧改编等不同创作领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常以公众人物、外交使节等身份出现,使得作家在文学创作手法、题材、主题等方面更加多元化。
其次,文学作品形式结合主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福克纳研究中最突出的是意识流叙述手法或现代主义形式实验,以及基于南方蓄奴制的种族和性别研究,而对于美国浪漫主义文学遗产中的罗曼史诗学及其文化阐释,以及南方文学的种植园罗曼史传统在福克纳小说中的传承与改造问题,学界的关注度明显不足。以“福克纳的家族”为核心议题的2019年度“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塔法”国际研讨会上,英美学者依然继续着传记式批评、手稿对比以及家族主题研究,并未探察到家族罗曼史在福克纳创作中更重要的形式与主题意义。
再次,福克纳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契合性问题值得研究。1942年以后,福克纳更多地介入社会公共活动,文学创作中也存在较多影射的迹象,比如《大宅》中琳达帮助黑人学校改善师资,反而遭到抵制的场景,很可能是对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过后南方教育领域破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一种回应。同时,白人贵族后裔过于沉溺于家族历史,不过是对社会现实表达不满的另一种方式。福克纳的后期创作既是回避现实的一隅净土,又可作为间接的社会批判,而家族罗曼史恰好承载了这样的文学功能。
有鉴于此,本书以美国南方文化传统中较为典型的家族罗曼史为切入点,分析福克纳后期创作中的家族叙事及其人物塑造中的身份建构,探讨作家在获得一定文学经验积累之后对南方题材的深度开掘策略,尝试解读福克纳文学创作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位与对话。
三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本书以福克纳创作中的家族罗曼史为聚焦点,考察后期作品中人物身份的塑成与国家认同问题。家庭是个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弗洛伊德的“家族罗曼史”理论是在精神分析的框架内考察个体对现实身份的不满与理想身份的想象,虽有父母和同胞兄弟姐妹组成的关系网络为背景,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依然重在思辨个人身份的生成与认知问题。有学者指出,精神分析方法对人的内心过于关注,“忽略了人的社会性”[104],因而有必要将家庭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每位成员的言行都受到其他成员影响,反过来又对他们施加或隐或显的影响。换句话说,人的身份建构首先缘起于家庭中的亲子和同胞关系,家庭环境对于理解个体身份具有重要意义。[105]不同的家庭会因成员个体差异而表现出多样性,这一点在福克纳的家族罗曼史书写中显得非常重要。家庭系统理论强调家庭的整体性,有利于分析亲子与同胞之间的利益与情感互动,但它游离于更为广阔的家族历史意识和人物关系框架。家庭系统更宜拓展为一张纵向历史延展、横向宗族结构扩展的家族关系网络。正是在这样的人物关系中,福克纳融入了历史与记忆、种族与性别、阶级与国家认同等宏大主题。本研究建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美国南方文学和福克纳研究成果,着重分析福克纳家族罗曼史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罗曼史对应的英文是romance,是在综合目前学界已有的传奇、浪漫小说、罗曼司等不同汉译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这一特殊文类蕴涵的历史意识之后得出的。在不同语境中,该词会与其他单词构成更具体的术语,如骑士罗曼史(chivalric romance)、中世纪传奇(medieval romance)、历史罗曼司(historical romance)等。自中世纪兴起以来,罗曼史主人公的故事一般包含历险和爱情两个要素,直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节终点,基本不会偏离追寻叙事(quest narrative)的框架结构,以及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的心理机制。[106]罗曼史在严肃、崇高的叙事文本中会产生偏离主题的情节或场景,构成情节结构的缀段性,叙事因而蜕变为非线性模式,最终表现为作者的一种修辞策略。
罗曼史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中会附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因素。[107]美国学者蔡司(Richard Chase)在其代表作《美国小说及其传统》(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1958)中,围绕研究对象的“创新性与美国性”展开论述,旨在证明如下事实:“美国小说从一开始,形式上便具有创新性和特色,通过融入罗曼史的元素而找准了后来的走向,界定了自我。”罗曼史意味着“可能摆脱小说对逼真性、发展性和持续性的一般要求”,“或多或少具有形式抽象性,伴随着某种触及意识底层的倾向”。[108]蔡司正式尊罗曼史为美国小说的“伟大传统”,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敌对阵营的确立,美国亟须在新的冷战国际秩序中重新进行文化定位,达到宣传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目的。[109]随着小说这一文类的蓬勃发展,罗曼史超脱了特定文类的规约,覆上相当程度的政治色彩。总的来看,罗曼史是一种意义异常丰富的文学形式。
家族罗曼史(family romance)的概念由弗洛伊德在1909年首次提出,当时他为奥托·兰克(Otto Rank)的专著《英雄诞生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英译本1914年出版)撰写了序言。弗氏从个体心理发展的角度阐释儿童对父母身份的主观想象,探讨儿童成长的心理变化机制。他认为,儿童最初会将父母视作唯一的权威,而随着视野和交际范围的拓展,逐渐认识到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与他人的不同或差距。加之兄弟姐妹会在父母面前争宠,那些自感遭到父母怠慢的孩子会心生负面情绪。他们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亲生,这无形中强化了亲子之间的疏离感,如果进一步结合个人白日梦似的幻想,孩子们会以领主或庄园主等社会地位更高的人去取代身份卑微的父母。[110]可见,家族罗曼史凝结了儿童在心理成长期间不切实际的雄心与幻想,是弗洛伊德晚年时期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再度阐释。个体以家庭为单位,在与社会他者的横向比较中形成自我定位,因出身不同而产生报复心理,由此埋下社会问题的隐患。这一概念带有浓重的精神分析色彩,内涵丰富、应用性强。
福克纳小说以多角度叙事等现代主义手法见长,讲述的南方家族历史以特定方式参与地域历史的建构,跨越记忆与现实的写法赋予作品以家族罗曼史的属性。更确切地说,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是典型的家族罗曼史。本书中,家族罗曼史用来指代福克纳笔下不同阶级和种族背景的家族谱系构建及相互之间的互惠或对抗关系,它由美国南方历史悠久的骑士文化土壤滋生而来,兼具欧洲中世纪传奇和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存在样态,是现代主义文学理念影响之下南方家族文学的特殊表现形式。
家族罗曼史突出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家族之间的姻缘关系以及地缘政治。不同家族的荣辱兴衰既可视作南方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也见证着欧洲传统文化与新大陆文学文化的碰撞与交叠。如果我们结合20世纪上半叶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文学的文化背景,分析福克纳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便可发现其中渗透着一股强大的理想主义潜流。作家塑造了绅士、妇女、平民白人以及黑人等来自不同族裔、性别及阶级背景的人物,再现了美国南方本土文化对欧洲中世纪骑士风范的承传与再造,写法上融合了19世纪中期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家对罗曼史的推崇与弘扬。本书由家族罗曼史出发,选择八部后期作品以见微知著,重新审视福克纳的现代主义创作理念及多重表征,探讨人物身份的建构及其在冷战时期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意义与价值。
福克纳研究中常见到由南方人物直接上升或提炼出人类生存和前途命运问题,但是两者之间还存在国家认同问题。德勒兹和瓜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在《卡夫卡:走向小民族文学》(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1986)中重新发现了卡夫卡“小民族文学”的概念,从哲学角度用“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思想上升为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生存处境的阐释。然而,解域之前必须辖域,需要“对一个位置或局部加以圈定”。[111]虽然福克纳的文学创作不能完全归结于上述意义上的“小民族文学”,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解域与辖域思想非常具有借鉴性,对福克纳小说人物的国家认同研究很有启发。
人物众多是福克纳后期小说的一大特征。这可能与福克纳所受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看,作家有意淡化传统英雄人物事迹,转而强调(不止一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网络。[112]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之间的叙事位置关系与家族内部的人物关系结构相吻合,人物关系在话语和故事两个层面上实现了有机统一。同时,不同作品中可能会有同一个人物反复出现,这一手法对于推动情节发展、实现文本间的互文性、增强作家作品体系的统一性均具有重要意义。本书结合南方文学的家族文化特征,绕开弗洛伊德的家族罗曼史概念中精神分析的外延义,重点分析家族背景及相互关系对人物身心发展的多重影响,阐发福克纳作品折射的南方社会现代化进程所遇社会问题,重点立足于人物的国家认同。本书将分四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概述后期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中出现的不同家族,从祖孙、兄弟姐妹和婚姻关系的角度细察同一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因奴役、婚内外情感、收养等行为造成的族际关系。福克纳后二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去吧,摩西》这部小说占据着核心位置,由于麦卡斯林家族不仅承接前期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和《没有被征服的》的基本题材,也直接决定了《坟墓的闯入者》《大森林》《掠夺者》三部作品主要人物的复杂家族背景和相互关系。不同作品之间的互文性,主要表现于白人贵族及其混血后裔的身份复杂性,使得他们游走于不同作品之间而成为“跨文本人物”(transtextual characters)。名门贵胄的发迹与延续见证并影射着约克纳帕塔法县建成与拓围的历史,而家族代际之间的遗产传承,这种由祖先到子孙的物质文化传递记录了白人族群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维护与传布。除了时间轴上的纵向传递,家族成员之间的横向关系——兄弟姐妹之间或合作或冲突的关系决定了家族传承的多元化道路,不同种姓的联姻、奴役及其他社交活动使得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家族关系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形成了树状格局(family tree),其中并非白人嫡系一枝独秀,而是多元、杂糅的人物关系网络。
第二章聚焦于女性人物的身份问题。她们位于家族系谱的交叉点,是人物关系复杂化的关键,这在麦卡斯林家族始祖的婚生子女、混血后裔以及与埃德蒙兹和普利斯特两个联姻支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与前期作品相比,福克纳这一时期对南方淑女形象的刻画大为减少,将关注的焦点从婚恋转向家庭与工作、社交、社区服务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使是在家庭婚姻问题上,作家特别突出了人物过去的言行对后来家庭生活造成的持续性影响。这在《修女安魂曲》女主人公坦普尔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延续了《圣殿》中暴力犯罪受害者的角色,内心矛盾与思想斗争展露无遗:个人感情上的一时失足造成婚后家庭生活不可挽回的伤害——次子遭杀。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过去与社区历史的对位呈现,后者对于女性的道德压制也在叙事结构上有所体现:三幕戏剧部分各冠之以一篇散文,分别叙述杰斐逊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创建历程。女性形象的变化还体现于《大宅》中的琳达身上,这部斯诺普斯三部曲末作的主要社会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女性走出家庭选择就业,由此产生夫妻和亲子关系变化,进而对南方社会产生深重影响。另外,老年女性形象不再扁平化,她们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帮助幼弱群体,维护南方的正面形象。
第三章着重探讨家族关系的跨种族构成问题,主要分析白人贵族在与美洲原住民、黑人、犹太人等不同族裔群体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权力关系。该章首先辩证分析“白人负担”这一西方文化命题,虽然吉卜林的原意含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一旦置于美国南方历史与社会背景中,福克纳的家族罗曼史创作便带上了新的含义和反讽意旨。然后,该章以《小镇》为个案分析了20世纪早期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种族关系,探察弃儿现象背后的亲属缺位与虚构亲属关系的形成。本书以拉特利夫及其家族的旅居经历为基础,讨论约克纳帕塔法县内犹太人在美国南方的国家认同历程。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充满白人与不同族裔混居而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南方文化本身就是杂糅、多元而开放的。
第四章的中心议题是南方家族融合背景下的阶级对立与消解,主要考察福克纳后期小说中的种植园贵族与穷白人家族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化,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方社会转型,深入探讨历史或记忆之于人物国家认同的意义。该章由打猎活动对于贵族、贫民等不同阶级的意义展开论述,分析其经济与符号功能,由此延伸至阶级差异与融合。有关斯诺普斯三部曲中明克与弗莱姆的冲突与决斗,本书从家族背景之下兄弟冲突发掘不同阶级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与对立,发现作家并不赞同以暴制暴的解决方案。人物的阶级身份替代了早期小说中截然不同的种族差异,表现了作家倡导的渐进主义身份融合构想,为国家认同奠定前提和基础。
福克纳后期作品中的南方家族是各种人物和社会力量相交与角逐的场域,融历史、地域、种族、性别和阶级差异于一炉,客观上促成了人物反思过去、寄望未来、强化国家认同,同时也为作家重塑家族罗曼史、表达艺术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载体。福克纳在现实生活中是小说家,穷其一生模仿曾祖父——老法克纳(William Clark Falkner),梦想成为一名“现代贵族”,“在小说中批判旧南方,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又模仿他们”[113]。福克纳不仅拥有曾祖父的名字,同样追求贵族生活方式:占有大量土地,蓄奴、骑马、打猎,驾驶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这样的人生追求融合于文学创作上的致臻完美理想,如福克纳为1954年兰登书屋出版的《福克纳读本》撰写的序言所示:
人总有一天会消亡,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在冷冰冰的印刷文字里茕茕孑立着本身就无懈可击(invulnerable)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人类心灵和肉体中一直激发出亘古不变、生生不息的激情。虽说有些心灵与肉体的所有者、保管者已经远逝,其后几代人却依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依然罹受着同样的苦痛(generations from even the air he breathed and anguished in)。如果人们过去曾经成功地得以励志,不言自明的是,即使人类只剩一个死僵且渐愈暗淡的姓名,鼓舞人心的事物永恒不灭。[114]
在他看来,作家的职责与贡献正在于写出“无懈可击的东西”,通过激扬文字去“鼓舞人心”,这样的信念与抱负正是福克纳利用四十年时间书写南方家族的最好注脚。“同样的空气”和“同样的苦痛”既是作品体系中上至先祖下至玄孙“几代”人共同的遗产,也正是这些美国南方社会的虚构人物群像,叙说着作家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情怀,叙说他对人类苦熬与不朽精神的颂扬。福克纳与性格各异人物的衔接点,即树立了多个小说人物原型的曾祖父,他化身于沙多里斯、康普生、萨特潘、麦卡斯林乃至斯诺普斯等家族的主要人物。福克纳将家族记忆融入故乡的历史记载和风土人情,结合个人丰富的想象和革新性的叙事手法,描绘出一幅美国南方的家族风情画。
[1] 可参考如下著述Michael Millgate,William Faulkner,New York:Grove Press,Inc.,1961,p.101;Irving Howe,William Faulkner:A Critical Study(4th ed.),Chicago:Ivan R.Dee,Inc.,1991,p.283;Malcolm Cowley,The Flower and the Leaf:A Contemporary Record of American Writing since 1941,New York:Viking,1985,p.296;鲍忠明、辛彩娜、张玉婷:《威廉·福克纳种族观研究及其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2] Joseph Blotner,ed.,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New York:Vintage,1978,p.146.
[3] 兰登书屋未经作家本人同意,擅自定名为Go Down,Moses and Other Stories,后来再版时才改回作者原定名,也是沿用至今的标题。
[4] 《寓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福克纳在好莱坞工作期间开始构思,基于作家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参军入伍经历的所观所感,历经十余年创作才完成的。主人公是个耶稣式的人物,领导十二个士兵在法军战壕里游说发动兵变,遭到最高统帅也是这位士兵的父亲判决死刑。因为这部小说脱离了约克纳帕塔法的美国南方社会语境,并不符合本书探讨的家族题材,笔者将其排除。
[5] Stuart 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Stuart Hall,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w,eds.,Modernity and Its Fu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277.
[6] William Faulkner,Absalom,Absalom!Joseph Blotner and Noel Polk,eds.,Novels 1936—1940,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1990,p.311.
[7] James B.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eds.,Lion in the Garden: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1926—1962,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8,p.255.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段话在福克纳研究领域引用率极高,甚至有几部著作直接选取部分词语或短语为书名,如Doreen Fowler and Ann J. Abadie,eds.,“A Cosmos of My Own”: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 1980,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1;Elizabeth M.Kerr,William Faulkner’s Yoknapatawpha:“A Kind of Keystone in the Universe”,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83;Joseph R.Urgo,Faulkner’s Apocrypha:“A Fable”,Snopes,and the Spirit of Human Rebellion,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9。
[8] 该小说出版时经由福克纳的经纪人做了大量删减,原题为《坟墓里的旗帜》,完整本直到1973年才问世。
[9] Cleanth Brooks,William Faulkner:Toward Yoknapatawpha and Beyon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p.165.
[10] [美]弗莱德里克·R.卡尔:《福克纳传》,陈永国、赵英男、王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3页。
[11] James B.Meriwether,ed.,William Faulkner Essays,Speeches & Public Letters,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4,p.8.
[12] Arthur F.Kinney,“The Family-Centered Nature of Faulkner’s World”,College Literature,Vol.16,No.1,1989,p.83.
[13] Frederick L.Gwynn and Joseph L.Blotner,eds.,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5,p.285.
[14] Frederick J.Hoffman,William Faulkner(2nd ed.),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66,p.44.
[15]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6] James B.Meriwether,ed.,William Faulkner Essays,Speeches & Public Letters,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4,p.6.
[17] George Marion O’Donnell,“Faulkner’s Mythology”,Frederick J.Hoffman and Olga W.Vickery,eds.,William Faulkner:Three Decades of Criticism,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3,p.83;James B.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eds.,Lion in the Garden: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1926—1962,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8,p.255;Malcolm Cowley,ed.,The Portable Faulkner,New York:Penguin,1946,p.ⅩⅨ.
[18] Emory Elliott,ed.,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906.
[19] Joseph Blotner,ed.,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New York:Vintage,1978,p.122.
[20] 在现代主义断代问题上,国内外学者莫衷一是。例如布拉德伯里和麦克法兰倾向于以1930年为界(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eds.,Modernism 1890—1930,New York:Penguin,1976),我国学者盛宁也基本认可这种看法(《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而叶廷芳和黄卓越则认为现代主义结束的标志在于60年代前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从颠覆到经典——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群像》,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参考Richard H.Pells,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Cultur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Depression Years,New York:Harper & Row,1973,p.ⅩⅣ;Emory Elliott,ed.,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695;Chris Baldick,The Modern Movement,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p.4。
[21] Doreen Fowler,Faulkner’s Changing Vision:From Outrage to Affirmation,Ann Arbor:UMI Research Press,1983,p.2.
[22] Joseph Blotner,ed.,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New York:Vintage,1978,pp.391,452.
[23] James B.Meriwether,ed.,William Faulkner Essays,Speeches & Public Letters,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4,p.120.
[24] Wayne C.Booth,Critical Understanding: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Pluralis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p.268-271.
[25] David Rampton,William Faulkner:A Literary Life,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1.
[26] John Bassett,William Faulkner: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5,p.2.
[27] David Minter,William Faulkner:His Life and Work,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92;André Bleikasten,William Faulkner:A Life Through Novels,Miriam Watchorn,tran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7,p.324;Daniel J.Singal,William Faulkner:The Making of a Modernist,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p.256.
[28] Michael Millgate,The Achievement of William Faulkner,London:Constable,1966,p.210.
[29] David Minter,William Faulkner:His Life and Work,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92.
[30]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1页。
[31]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
[32] Joseph Blotner,ed.,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New York:Vintage,1978,p.122.
[33] André Bleikasten,William Faulkner:A Life Through Novels,Miriam Watchorn,tran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7,p.368.
[34] Lawrence H.Schwartz,Creating Faulkner’s Reputation:The Politics of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8,p.4.
[35] John N.Duvall,“An Error in Canonicity,or A Fuller Story of Faulkner’s Return to Print Culture,1944—1951”,Faulkner and Print Culture: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2015,Jay Watson,Jaime Harker,James G.Thomas,Jr.,ed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7,pp.123-126.
[36] Maurice Edgar Coindreau,The Time of William Faulkner:A French View of Modern American Fiction,George McMillan Reeves,ed.& trans.,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1,p.51.
[37] Mauri Luisa Skinfill,“Modernism Unlimited:Class and Critical Inquiry in Faulkner’s Later Novel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9.
[38] Michael Kreyling,Inventing Southern Literatur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p.148.
[39] Peter Swiggart,The Art of Faulkner’s Novel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2,p.174.
[40] Daniel J.Singal,William Faulkner:The Making of a Modernist,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p.256.
[41] David Rampton,William Faulkner:A Literary Life,Basingn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151.
[42] Theresa M.Towner,“The Roster,the Chronicle,and the Critic”,Faulkn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2000,Robert W.Hamblin and Ann J.Abadie,ed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3,p.8;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43] James Gray Watson,The Snopes Dilemma:Faulkner’s Trilogy,Coral Gables,FL.: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68,pp.12-13.
[44] Joseph Blotner,“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Faulkner’s Life and Art”,Faulkner and Idealism:Perspectives from Paris,Michel Gresset and Patrick Samway,S.J.,ed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3,pp.17-25.
[45] Kenzaburo Ohashi,“‘Motion’ and the Intertextuality in Faulkner’s Fiction”,Intertextuality in Faulkner,Michel Gresset and Noel Polk,ed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5,p.159.
[46] Hans H.Skei,“William Faulkner’s Late Career:Repetition,Variation,Renewal”,Faulkner:After the Nobel Prize,Michel Gresset and Kenzaburo Ohashi,eds.,Kyoto:Yamaguchi Publishing House,1987,pp.248-251.
[47] Taylor Hagood,Following Faulkner: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Yoknapatawpha’s Architect,Rochester:Camden House,2017,p.12.
[48] Robert Penn Warren,“William Faulkner”,William Faulkner:Three Decades of Criticism,Frederick J.Hoffman and Olga W.Vickery,eds.,New York and Burlingame: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3,p.109.
[49] Joseph Blotner,ed.,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New York:Vintage,1978,p.185.
[50] Joseph Blotner,ed.,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New York:Vintage,1978,p.299.
[51] Flannery O’Connor,Mystery and Manners:Occasional Prose,转引自Margaret Donovan Bauer,William Faulkner’s Legacy:“What Shadow,What Stain,What Mark”,Gainesville,FL.: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5,p.1。
[52] Donald M.Kartiganer,“Quentin Compson and Faulkenr’s Drama of the Generations”,Critical Essays on William Faulkner:The Compson Family,Arthur F.Kinney,ed.,Boston,Massachusetts:G.K.Hall & Co.,1982,p.381.
[53] 费孝通:《乡土中国》,[美]韩格理、王政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54] Claudia Durst Johnson,ed.,Family Dysfunction in William Faulkner’s“As I Lay Dying”,Detroit:Gale,2013.
[55] Irving Howe,William Faulkner:A Critical Study(4th ed),Chicago:Ivan R.Dee,Inc.,1991,pp.8-9.
[56] William Faulkner,The Mansion,Novels 1957—1962,Joseph Blotner and Noel Polk,eds.,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1999,pp.409-410.着重号部分原文为斜体。
[57] Chris Baldick,The Modern Movement,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pp.173-176.
[58] James B.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eds.,Lion in the Garden: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1926—1962,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8,p.49.
[59] 王万顺:《论“长河小说”源流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2期。
[60] 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7页。
[61] 卢敏:《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道德主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0页。
[62] Patricia Drechsel Tobin,Time and the Novel:The Genealogical Imperativ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7.
[63] Jobst Welge,Genealogical Fictions:Cultural Periphery and Historical Chang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5,pp.196-200.
[64] 李杨:《颠覆·开放·与时俱进:美国后南方的小说纵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65] Richard Gray,Writing the South:Ideas of an American Reg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Ⅻ.
[66] H.L.Mencken,“The Sahara of the Bozart”,Defining Southern Literature:Perspectives and Assessments,1831—1952,John E.Bassett.ed.,Madison: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97,p.285.
[67] Louis D.Rubin,Jr.,The History of Southern Litera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61-262.
[68] Richard H.King,A Southern Renaissance:The Cultural Awakening of the American South,1930—195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27.
[69] Robert O.Stephens,The Family Saga in the South:Generations and Destinies,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52.
[70] Arthur F.Kinney,“Faulkner’s Families”,A Companion to William Faulkner,Richard C.Moreland,ed.,Malden,MA.:Blackwell,2007,pp.180-201.
[71] Gwendolyn Chabrier,Faulkner’s Families:A Southern Saga,New York:The Gordian Press,1993,p.Ⅺ.
[72] Mark Leaf,“William Faulkner’s Snopes Trilogy:The South Evolves”,The Fifties:Fiction,Poetry,Drama,Warren French,eds.,DeLand,FL.:Everett/Edwards,inc.,1970,pp.52-54.
[73] John T.Irving,Doubling and Incest/Repetition and Revenge:A Speculative Reading of Faulkn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p.43.
[74] Gary Storhoff,“Faulkner’s Family Dilemma:Quentin’s Crucible”,William Faulkner:Six Decades of Criticism,Linda Wagner-Martin,ed.,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p.236.
[75] Jay Watson,“Genealogies of White Deviance:The Eugenic Family Studies,Buck v.Bell,and William Faulkner,1926—1931”,Faulkner and Whiteness,Jay Watson,ed.,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1,p.21.
[76] Michel Gresset,“Home and Homelessness in Faulkner’s Works and Life”,William Faulkner:Materials,Studies and Criticism,Vol.5,No.1,1983,pp.26-42.
[77] Rosalie Murphy Baum,“Family Dramas:Spouse and Child Abuse in Faulkner’s Fiction”,The Aching Hearth:Family Violence in Life and Literature,Sara Munson Deats and Lagretta Tallent Lenker,eds.,New York:Insight Books/Plenum Press,1991,p.222.
[78] Carolyn Porter,“Faulkner’s Grim Sires”,Faulkner at 100:Retrospect and Prospect,Donald M.Kartiganer and Ann J.Abadie,ed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0,pp.120-121.
[79] Mark Allister,“Faulkner’s Aristocratic Families:The Grand Design and the Plantation House”,Midwest Quarterly,Vol.25,No.1,Autumn 1983,pp.90-101.
[80] Joseph Blotner,“The Falkners and the Fictional Families”,The Georgia Review,Vol.30,No.3,Fall 1976,pp.574-592.
[81] David Minter,William Faulkner:His Life and Work,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3.
[82] Doreen Fowler,The Father Reimagined in Faulkner,Wright,O’Connor,and Morrison,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3.
[83] Deborah Clarke,Robbing the Mother:Women in Faulkner,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13.
[84] Noel Polk,Children of the Dark House:Text and Context in Faulkner,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6,p.29.
[85]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
[86] Valérie Loichot,Orphan Narratives:The Postplantation Literature of Faulkner,Glissant,Morrison,and Saint-John Perse,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7,pp.2-3.
[87] Lynn Hunt,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1-16.
[88] Eric J.Sundquist,Faulkner:The House Divide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89]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90]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91]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92]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93] 武月明:《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4] 高红霞:《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及其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重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95] 高红霞:《福克纳家族小说的“寻父—审父”母题》,《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96] 高红霞:《福克纳〈去吧,摩西〉账本叙事的史笔诗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97] 高红霞:《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的母题类型及其矛盾性》,《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98] 曾军山:《论斯诺普斯三部曲与南方骑士文化的互文性》,《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黄秀国:《叩问进步——论福克纳穷白人三部曲中的商品化与异化》,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谌晓明:《从意识洪流到艺术灵动——福克纳的斯诺普斯三部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韩启群:《转型时期变革的多维书写——福克纳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物质文化批评》,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99] 韩海燕:《威廉·福克纳和曹雪芹作品中的年轻女性》,《求是学刊》1985年第2期。
[100] 肖明翰:《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1] 肖明翰:《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
[102] 张之帆:《莫言与福克纳——“高密东北乡”与“约克纳帕塔法”谱系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
[103] James Gray Watson,The Snopes Dilemma:Faulkner’s Trilogy,Coral Gables,FL.: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68;Joseph R.Urgo,Faulkner’s Apocrypha:“A Fable”,Snopes,and the Spirit of Human Rebellion,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9;韩启群:《转型时期变革的多维书写——福克纳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物质文化批评》,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04] 顾悦:《超越精神分析:家庭系统心理学与文学批评》,《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105] John V.Knapp,Critical Insights:Family,Ipswich:Salem Press,2013,p.Ⅶ.
[106] 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1957,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pp.186-203.
[107] Barbara Fuchs,Romanc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4,pp.4-11.
[108] Richard Chase,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London:G.Bell and Sons Ltd.,1958,pp.Ⅶ-Ⅸ.
[109] Lawrence H.Schwartz,Creating Faulkner’s Reputation:The Politics of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8,p.4;John McWilliams,“The Rationale for ‘The American Romance’”,Boundary 2,Vol.17,No.1,1990,p.73.
[110] Sigmund Freud,Collected Papers,Vol.5,James Strachey,ed.,New York:Basic Books,Inc.,1959,pp.75-76.
[111] 陈永国:《理论的逃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30页。
[112] Alex Woloch,The One vs the Many: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Novel,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38.
[113]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
[114] James B.Meriwether,ed.,William Faulkner Essays,Speeches & Public Letters,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4,p.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