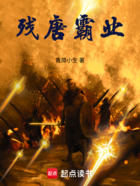
第18章 借风之力
青口河畔,龙武军左厢大营。
军情如火,长史胡安以及四位军指挥使尽数齐聚帅帐。
整整一刻钟,帅帐中始终保持着令人屏息的缄默,他们安静地看向主座,李昭正忖眉思索,手指不断在张景的信笺折痕处反复摩挲,脸色一阵铁青。
“末将、末将,着实对不住虞候!此番鲁莽行事致使流民尽丧,还请虞候责罚!”
早已卸去甲胄的张轶,重重跪倒在案前,发髻紊乱、满脸疲惫,而受创的右肩还在渗血。
李昭抬眼看去,这个自幼便与自己形影不离的兄弟,此刻宛如被抽了脊梁骨的困兽,浑身狼藉,似乎这一遭令他失去了往日的高傲心气。
“张指挥使,你可知此番你罪在何处么?”
张轶闻言并未动弹,而是继续伏地颤声道:“末将愧对虞候厚恩,向来无能却一贯自负,此番不听父言小觑来敌,不仅流民亲兵尽折,更令契丹警觉导致战机已然错失,诸多准备前功尽弃!耽误虞候大计,末将实罪不可赦,但凭虞候处置!”
“看来你还是不解。”
李昭平静地摇了摇头:“亲兵献身护你乃是天职,至于那帮流民,终究是戴罪之身,死了倒也偿还他们袭城的罪孽。而契丹人被惊动亦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我既敢派你们前去打探,心中便已做好准备,此一节算不算前功尽弃尚未可知。”
“我真正恼的,是你张轶竟胆敢不守军令擅自行动!早知你性情鲁莽,又自持勇武,故而我才令你阿爷领军,万万没想到你阿爷也未能制得住你......”
张轶浑身一颤,蓦然抬头焦急道:“虞候明鉴!此事乃是末将一人之错,实与我阿爷无关啊!还请虞候重重降罪!”
“呵,你看,又急!我可没说放过你。”
李昭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过头问道:“胡安,你是我军中长史。依照我朝军律,这张轶该当如何处置?”
正在沉思的胡安闻声猝不及防,正当起身拱手,却又瞥见李昭若有若无的拧眉,瞬间会意,随后清了清嗓子。
“咳咳......禀虞候,依照军规,张指挥使当降职三级,帐前杖二十。”
李昭皱眉又道:“你莫不是因他是我的家将,故意说轻了?”
胡安暗自腹诽了几句,随后又坦然笑道:“虞候,在下得虞候信重作为长史,掌佐军中律例杂务,岂敢渎职虚言、妄改军制?”
“张指挥使此番擅自行动是不假,但其父张景身为主将,却不能尽到督管约束部下的责任,亦有罪责,但张景到底保住了所部全军,几无损伤,故又可功过相抵。”
“所谓议罪分主次,刑罚各分摊。两相权衡,张指挥使应处降职杖刑最为合理。”
“杖二十自不可免!可如此行事,焉能为将?”李昭若有所思,随后挥手道:“着革去张轶亲军指挥使一职,以昭武校尉身留帐听用。”
“末将,谢虞候!”张轶俯首叩拜,随后利落地起身来,从容地被两名亲军押出了帐外,反倒面色稍稍释然。
不久,帅帐外便传来呼哧有力的噼啪声,声声入肉惊得众将面面相觑,不想李虞候竟未宽容家将,不由得暗自感叹。
李昭抬手指向帐外,肃然道:“众将往后必遵令行事,当以张轶为诫!”
胡冲、周继、陈诲以及张彦卿四人急忙起身,答:“末将遵命!”
眼看张轶的事情暂且告一段落,李昭抿了口茶汤,又问道:“如今军情明了,已摸清契丹贼兵驻于吴山北麓,接下来我大军该如何行动?诸将有何意见,但可说来。”
胡冲到底忍不住,先发声为老友做了辩护:“虞候,末将虽见浅,但却不得不说一句,张景不愧为沙场老将。”
“既没有鲁莽与契丹人交战保全了军队,又在我大营未得军情前,为防止契丹人南下突袭先占住了沙集驿这个要害隘口,此战能否延续关键在于此举。”
周继则与张彦卿相视了一眼,随后起身道:“虞候,按照原先所谋,张景一部只受命先行沿路打探,待得敌情后,再由虞候率全军北上突袭,但如今贸然惊敌,契丹人必有防备,我军恐难功成。”
“周指挥使所言持重可取。”
向来沉默寡言的陈诲亦点了点头,继续道:“但末将不仅认为,虞候不能再继续贸然进军,或也没有出兵的必要,那契丹人如今乃是在吴山北麓设营,所在已非我大唐境内。”
“须知伪晋山东正在鏖战,我军若突入敌境,不仅有难测之危,若是闹大了,枢密院那边......恐也难交代。”
四位军指挥使都一一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且各有理有据,胡安在一旁仔细聆听摘录,心里为之惊喜,随后看向李昭道:“虞候,几位将军不负其职已陈述己见,不过最终还是要虞候拿主意。”
众将闻言齐齐点头,却见李昭淡淡一笑:“你们都说得很好,但我意已决,进军计划不变,只是一些细节需要改改。留一军步军驻守大营,其余各部随我北上击胡!”
“虞候但有所命,末将誓死相从!”胡冲头一个出声响应。
周继和张彦卿亦赶忙起身:“末将也是!”
“虞候三思!”
胡安想了想,劝说道:“虞候,请恕在下多言!且不说如今战机已经错失,而且从张景所部能够安然退出吴山,又能在沙集驿休整一个昼夜的情形来看,契丹人或许根本没有再度南下之意。要知道吴山距离沙集驿不过二十里,契丹轻骑若想追击,瞬发可至。”
陈诲附和道:“长史说得不错!虞候,这些契丹人远离本土数千里之遥,起初是因援杨光远而来,但青州此刻已陷入伪朝大军重围,迟早必定败亡,没了盟友,契丹人又岂不懂孤军深入不可久持的道理?”
“况且他们在山东已劫掠两三月,前番又南下怀仁城追杀了一大波流民,财物人丁斩获颇丰,末将认为他们定会迅速北返,说不定我大军北上之时,契丹人已然撤离,许会徒劳无功。”
“陈指挥使,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李昭听完连连点头不吝赞赏。
“末将不敢。”
“但,”
李昭忽而变了脸色,拍案道:“想数十年以来天下分裂、中原无力,致使胡虏肆虐苍生。那契丹,不过草原小小一蛮族,昔日盛唐之贱奴,今竟敢视我汉人如猪狗,这是何等悲哀!”
“诸位莫忘了,我大唐虽偏安承平,但兵祸加诸于天下,我等又焉能幸免?更别说契丹狗刚刚在怀仁城外屠戮近万!”
“那些横死的流民虽是北人,却亦与吾等同种同族,我既为海州屯营,岂能坐视外敌犯境又安然退去?”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必诛之!”
“虞候大义!末将谨记!”陈诲起身,深深一礼,其余三将亦是心潮澎湃。
李昭顿了顿,又问道:“我且有一问考考你们,契丹人此时因何驻扎在吴山北麓,所在正好是两国交界,而非直接北返?须知契丹出兵向来不靠辎重,而以掳掠行军,既可一路北上,何必又迁延在此扎下营地?”
胡安忽而有所领悟:“事出反常必有诡,契丹不走,莫非他们除了掳掠,还有战事要继续?!”
“正是!”
李昭点了点头,看向陈诲道:“故而我和陈指挥使的看法不同,我认为那杨光远虽然败象已现,但却没那么快能被击败,青州纵使粮尽,却仍有兵五万,口十万户,反叛乃是绝路,又岂是好给予之辈?”
“加上伪朝新帝石重贵即位后,与其父石敬瑭行事截然不同,反而拒绝臣事契丹,此刻山东自乱不暇,契丹人的兵马都深入到江淮来了,河北前线又怎能没有兵事?”
“两线交战,伪朝疲弊,我料纵使最后得胜,亦是惨胜,元气大伤则现亡国之象......总之短时间内,青州必不能下!”
“青州难破,契丹便会妄想与杨光远重新联手生事,所以吴山这群狡猾的契丹狗必是在观望,加上契丹向来小觑汉人,况乎我南人!”
“先前张轶仅以身免,而后张景紧急撤军,倒是阴差阳错地示敌以弱,反而是个进军的绝佳机会!”
众将听罢心服口服,齐声拜道:“虞候英明!”
老将胡冲向来好战,忍不住又问道:“虞候,既要战,又该怎么个战法?那契丹人就算轻视我等,经了张轶这一遭肯定也会加强警备,契丹出身游猎,不仅善骑更多弓手,林地简直是他们天然的猎场......”
“这有何难?既然森林是他们的猎场,那就毁了这座猎场便是。”
李昭倒是颇为淡定,挥了挥手道:“胡安,本将命你即刻赶赴海州城,请陈刺史立即遣人将城里所有的猛火油都给我全部运过来!”
“猛、猛火油?!”
众将大为震惊,胡冲急忙提醒道:“虞候,那猛火油不是用来守城的么?”
周继也慌忙道:“是啊虞候!此物太过凶险,遇水亦不可阻啊!吴山多密林,一旦风起牵连己军,后果不堪设想啊!”
“慌什么?”
李昭淡淡道:“契丹在北,我在南,引火时借一道南风不就行了。”
“啊?”众将再度震惊。
尤其是胡冲,作为从小看着李昭长大的家将,怎从未听说自家大郎君还有这等本事?显然有些不可思议,于是犹豫了片刻说道:“虞候,你这是要模仿周郎火烧赤壁?可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是真是假暂且不说,这风乃天定,哪能说借就借?”
倒是胡安满脸兴奋道:“虞候,莫不是还会观星奇门之术?”
“奇门遁甲谈不上,不过看看天象还是可以的。”
李昭摊手笑了笑,却不准备故弄玄虚,于是坦诚道:“尔等不必惊疑,我必不会拿全军上下的性命说笑,我等即将并肩作战,为免你们举棋不疑,便与你们大概说说。”
“来海州之前,我先前恰好在家父书房中查阅过一奇书,道是淮北近海之地,入冬偏北风,至夏吹南风,开春则多偏东风。如今时至五月,吴山当以南风为主。”
“竟有这等说法?”胡安一脸茫然,又好奇地追问道:“那是何等奇书?莫非是诸葛武侯佚散之作?!”
李昭还未想好怎么编,却见胡冲一把兴冲冲地接过话来:“你管他是谁的书!既是我家相爷的藏书,那便绝不会有错!虞候果然类父祖,处事总有先见之明!”
“咳咳!”李昭尴尬地笑了笑,又严肃补充道:“当然,虽是以南风为主,我却也难以预料是何日几时,故而为以防万一,到时候全军先于沙集堆设营驻扎,先悬高旗测风向,寻日烈南风起时便立即进军。”
“这一回,誓将契丹人统统挫骨扬灰!”
众人齐齐起身:“遵命!”
注:《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收录了自甲骨文时代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各地的气象记录,包括风向、天气现象及相关历史事件。根据历史天气数据,淮北在五月的风力大多在1-4级之间,风向主要为东南风和南风,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