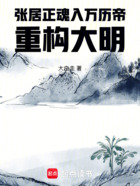
第59章 大局已定 上
“朕为何要将胥吏改成流官?这也是朕的无奈之举。
胥吏存在地方多少年,你们心里清楚的很。
当然,这其中必然有他存在的缘由。
可如今当下大明朝,乡绅与胥吏之间的勾连已经到了目无王法的地步。
纂改黄册,篡改鱼鳞册,威逼利诱那些无权无势的乡民,甚至将一县知县的权力架空。
他们架空的是知县吗?那是朝廷!”
朱翊钧的声音震耳欲聋,字字见血。
而跪地的几人听了心惊胆战,瑟瑟发抖。
他们对于这些事情心如明镜。可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任何办法。
朱翊钧缓步来到金台,歪着身子斜倚在书案上,目光在殿内人的身上一一掠过,无奈叹了口气。
乾清宫内的这些人是推崇改革的,唯独做事太过谨小慎微。
当然,谨小慎微并不是坏处。
但是过于小心谨慎,只能医治大明的表象,无法渗入肌理。
朱翊钧清楚他们的顾虑,担心走错一步,便将大明二百余年的基业毁于一旦。
可大明朝若是继续这样颤颤巍巍走下去,还能撑得了多少年?
五十年?一百年?
朱翊钧思及于此,一双眸中泛着点点亮光。
旁边的小太监立刻送上一方锦帕,朱翊钧摆手退去。
他定了定神继续道:“胥吏不改,地方难治!各位爱卿……朕意已决,但朕也顾及各位爱卿所虑,先拿长清县作为试探。
至于成败与否,咱们君臣就看长清县这几年的政绩,如何?”
跪地的众人一听,也就不敢再劝谏,纷纷叩首:“臣,遵旨!”
这时,天上的厚云随风而去,之前遮住的阳光射进乾清宫一丈距离。
墨色的地砖泛着耀目的亮光,殿内瞬间亮堂起来。
朱翊钧看了一眼泛着白芒的地砖,神色也好了许多。
“各位爱卿……长清县县衙被砸,一切文书都已经烧毁,其余文书还可慢慢补充,那户册与鱼鳞册需得立即补齐。
着济南卫出兵入驻长清县,一则丈量全县田亩,二则盘查全县丁口。
日后长清县就以这次查清的户册及鱼鳞册为依据,征收两税。
县衙六房胥吏皆从外省挑选合适人选,杂役差役可从本地挑选。
但户房的杂役必须从军中挑选调派,以来配合胥吏征收田赋。”
丈量田亩及胥吏身份,这两件事最是重要,也最是紧迫。
至于钱庄改革一事,目前来看还是稍稍往后放一放。
如今只要长清县新任的胥吏能顺利接手县里的事务,那么钱庄的改革也就水到渠成。
只有这样,后续的一些改革,也就能在长清县逐步展开。
朱翊钧何曾不也是小心谨慎,一点点儿向前试探着迈步?
他的谨慎,潘晟也感觉出来。
长清县有了卫所兵士驻扎,那就掀不起大的风浪。
所谓万事开头难,皇上的这个开头最起码算是稳妥。
潘晟见事情尚在掌控之内,也就安下心。
他想到丈量田亩后的一些事情,便又问道:“皇上,若是清查出有隐匿田亩的乡绅,该如何处置。”
“凡隐匿田亩者,皆交予知府衙门依照大明律判罚。”
朱翊钧的打算,是把这个棘手的事交给县衙上一级知府衙门。
如今改革初期,知府衙门有卫所兵士,这个锅还是先让知府来背。
这样大大避免了地方与知县的直接冲突。
身为内阁首辅的潘晟慎重思忖一番,缓缓伏地叩首:“臣遵旨!”
此举一出。
殿内人也就没有坚持的意义,余下的只有一些细节方面需要修补。
所有人再次纷纷叩首:“臣,遵旨!”
朱翊钧吁了口气,“众爱卿起来吧。”
“张爱卿,你的慎重很得朕意!”
朱翊钧心事已定,轻松了许多,便看向张学颜,先给了他一个蜜枣。
紧接着又道:“长清县以三年为期,若是此举改革导致长清县税收不如往年,朕必定取消这一政策,如何?”
皇上都这么说了,张学颜哪还有不从之理?
三年不也就三千两白银,就算打了水漂也是无所谓。
他躬身道:“皇上圣明!”
朱翊钧又来到申时行面前,拍了拍他肩膀,语重心长道:“申爱卿,你担忧乡绅反抗朝廷,属实多虑了。
乡绅的背后是哪些人,想必你也清楚,他们敢逆天而行?
呵呵……这个政令一旦发出,朝中许是出现一些不和的声音,但申爱卿你从来都不会让朕失望的。”
又是我?
申时行心中暗吐苦水,余有丁顿时松了口气。
所有人都知道,像这种政令都是先由大臣替皇上提出。
若是政令实施顺利,那是皇上圣明,高瞻远瞩。
若是政令行不通,一切的罪责皆由这位大臣承担。
申时行苦笑一声,低垂着头应道:“回皇上,微臣脸皮算是厚,还能应付得来。”
“哈哈哈……”
朱翊钧满意地笑了笑,又拍了拍他肩膀,“有申爱卿在内阁为朕分忧,大明怎能不兴?”
给申时行的这个甜枣,带着点苦涩。
“梁爱卿?”
朱翊钧看向梁梦龙,“圣旨过些时日会到济南府,你再给刘通及那位新上任的知府孙德武去一封信,交代好从济南卫挑选兵士的事宜。”
梁梦龙躬身应道:“臣遵旨。”
“余爱卿,你与万爱卿仔细讲讲京中的一些事,他刚接任都察院,难免有些慌乱,你在旁边帮扶着,朕放心!”
朱翊钧的目光从余有丁的脸上移向万顺甫,“万爱卿,今日你回去好好休息,后面的日子有你忙的。”
余有丁也是苦笑一声,他本以为有申时行在前面顶着,自己正好抽身远离是非。
谁知皇上竟然是让他去与万顺甫挡着言官,估计少不了挨骂。
余有丁无奈,给万顺甫递了个眼神,一同躬身:“臣遵旨!”
“行了,你们先去内阁拟旨。”
朱翊钧走回书案后,精神奕奕地坐在龙椅上,吩咐道:“潘爱卿留一下。”
众人识趣,纷纷退了出去。
潘晟如今对这位年轻天子又惊又喜。
惊得是,怎么看都不像这个年纪才有的城府。
而喜的是,大明朝有了这样一位既勤政爱民,又思虑周全的天子,岂能不兴?
众人渐渐离开,他站在书案前,垂着头等着皇上的吩咐。
朱翊钧抬头看他一眼,又看看空荡荡的大殿,笑道:“潘爱卿,朕留下你是想问一个让朕颇为头疼的问题,看看潘爱卿可有法子?”
潘晟躬身拱了拱手,“微臣愿为皇上分忧。”
“嗯!”
朱翊钧放下朱笔,双肘抵在书案上,像是一个勤学好问的孩子。
“大明开创之初,太祖皇帝将土地悉数分与百姓,为何只过了一二百年,百姓手中的土地就又重新回到了那些乡绅地主手中?”
潘晟对这问题再明白不过。
他也知道皇上心里更是清楚,这是让他这个臣子先开这个口。
“回皇上,土地便是百姓的财产,而财产永远都是向上汇聚,经年累月下来,底层的百姓手中的财产越来越少,而上面的乡绅则是越来越多。
每朝每代皆是如此,近千年来,哪个朝代也没有法子打破这个习惯,微臣亦是没有什么好的法子。”
潘晟开了这个头,把这个问题送回了朱翊钧。
朱翊钧笑道:“是啊,朕还有一点不明白,这财产为何会往上汇聚呢?”
潘晟望了一眼笑眯眯的皇上,只能又接过话来。
“回皇上,耕种看天,既然看天,就逃不过旱涝两灾。
到了灾年,作为百姓唯一财产的土地,长不出粮食,他们只能忍痛卖地,以求生存。
而作为有身份的地方乡绅,他们手中钱粮富裕,便可接收乡民田地,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下去,那些土地就自然而然的到了上面的乡绅手里。”
“是啊,总不能饿死吧。”
朱翊钧叹了口气,缓缓道:“只要让百姓不卖地,安心度过灾年,那这地就永远不会到乡绅手中。
朕为这个事情也是苦思冥想许久,终还是得出来一个法子,不知行得通还是行不通。”
这是要进入正题了。
潘晟立即打起精神:“微臣也想知晓皇上的法子,若是可以让百姓手中永远都有自己的田耕种,这可是天下百姓的大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