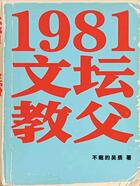
第7章 如何《活着》
杨百川还是不想放弃去市里参加联谊会的机会。
毕竟投稿《十月》只是脑子一热,是虚无缥缈的,而市里这次机会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回家的路上,他还在想着刚刚邮局营业员的那句“同志,你是作家?”,心里美滋滋的。
他不要脸地点点头,说酒厂厂报上那篇《遥远的海岛》就是自己写的。
那女人若有所思地挠了挠下巴,说:“不晓得。”
……
杨百川懒得理她,转身往家走。
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还没拧,门就吱呀一声打开了。
门缝里露出一张湿漉漉的白色的胖脸,两只肿泡眼像被雨水沤烂的樱桃。
“妈,你……”
“你个砍脑壳的背时娃儿啊,你跑哪里去了?”
韩家书冲上来,往杨百川的肩头狠狠捣了一下:“你老汉儿才出事没几天,你又不落屋(回家)了,是不是想我这个当妈的不活了……”说着呜呜地哭起来。
杨百川心里一酸,一阵歉意涌上来,把母亲抱住,闻见她后颈窝的樟脑丸味。
“你不想去找那个背时堂客就不去,啷个可以不回家……”
杨百川小声说:“妈,我错了。”
韩家书往后一仰,一双噙着泪的眼睛盯着他,好奇地打量:“你,你昨天晚上在哪里过的夜?”
杨百川说:“昨天我没困觉……”
话还没说完就被掐断:“没困觉?那你跑哪儿去了?”
杨百川把昨晚上的事说了一遍,看到韩家书脸上的神色软了下来:“幺儿不要太辛苦了,小说可以慢慢写嘛。”
他在母亲的背心里轻轻拍了几下:“晓得了,妈。”
接下来的几天,杨百川都在构思他那篇老孙版《活着》,打算写个精彩的中篇,在渝城文坛中打响名头。
就像后世写网文一样,他既然决定写一个翻版的《活着》,就得拆文,搞清楚《活着》这幢大厦是如何建成的。
读大学时背过的知识点,如车窗外的风景般飕飕闪过脑海。
在后世文学史上,《活着》被视为余华创作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转向通俗小说的标志。
这一转向的发生有很多因素。
就文学本身而言,先锋小说不具有可持续性。整天在叙事技巧上绕圈子,人称、视角、结构、语言、风格……能创新的只有这些,玩遍了也就没什么可玩的了。
后世有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不好好讲故事的人都是不会讲故事的人。
先锋小说作家通常缺乏老实讲故事的想象力,也没有观照现实的穿透力,说句不好听的,就只能在写作技巧上兜圈子、迷惑人。
所以有评论家认为,《活着》等作品的涌现,是先锋小说作家在向传统现实主义补课、取经。
就像画画一样,人家毕加索年轻的时候也是写实的大师,后来到了一定境界,才慢慢走向肆意的抽象创作。
而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作家是反过来的。
另一方面,读者不买账。
你成天写些云里雾里的玩意儿,谁特么看得懂?作者自己也讲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其实,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作家们常有类似的倾向,把自己束之高阁,把“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完全抛在脑后,抛弃了读者,还美其名曰搞艺术搞创新。
等他们发现自己无人问津时,为时已晚,他们也被读者抛弃了。
这也和社会变迁有关。在过去,作家都是吃官家饭的,而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腾飞,读者便成了作家们的衣食父母。
文学史家用“断奶”这个词来形容90年代作家与体制的关系,作家必须自己找奶喝。
所以说,《活着》也是重新拥抱读者的尝试。
但也不能说《活着》就完全回到了传统。这也是杨百川想在新的小说中模仿的部分。
就写作手法而言,《活着》采用了“重复”的手法。
主人公福贵的亲人以相似的“意外”相继离世,形成了死亡的循环。
福贵反复提及“鸡变羊、羊变牛”的生活愿望,却又反复回到贫穷、饥饿,在希望与幻灭中循环。
这有点类似于后世爽文的反面。
爽文是通过“危机-解除危机-装逼”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的循环,来营造爽感,让人越看越爽。
《活着》则是通过“危机-死亡”的模式来营造悲剧感,危机和死亡不断交替出现,让人陷入泥淖般越来越深的痛惜之中。
另一方面,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常赋予苦难一些其他的意义,比如,非得批判一下社会、教育一下读者。
要是读者看完小说,没感慨“啊,今后我一定痛改前非,努力做一个四有公民!”,就一定是白读了。《活着》却反其道而行之。
福贵的生存没有明确的“意义”支撑。他既不为复仇、抗争而活,也不为追求幸福而活,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这句话很绕,但消解了所有宏大的价值。
这是杨百川想在新小说里着重学习的一点,这可以使故事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悲剧。
第三方面,《活着》的历史观也比较特别。
《活着》横跨漫长的历史时期,却刻意回避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正面描写,始终聚焦于福贵这个平头百姓。
书中的细节都来源于福贵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抽象的历史概念。
在杨百川穿越前,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就像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尘,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讲的也是相似的道理。
但在那个年代,这种思维还是很独到的。
如果想的话,杨百川可以借此迎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浪潮。
但他不愿意。他想写一个活生生的孙德贵,而不是把他作为跟风的工具。
杨百川在书桌前坐了十个多钟头,从上午到下午,中途就吃了个饭,眯了一会儿,却一点没觉得疲惫。
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物关系网,以老孙为中心,周围环绕着他的亲人、朋友、敌人,仿佛一朵巨大的莲花。
再画了一条漫长的时间轴,将老孙的人生节点标注在上面。
他记得有一个作家说过,短篇写氛围,中篇写故事,长篇写命运。
要写好一个中篇,重要的就是组织好故事的结构,使之逻辑缜密、环环相扣。
他在做这样的努力。
窗外彻底黑了下来,昏黄的路灯亮起。他终于完成了那篇小说的大纲,并给它起了个富有哲理和诗意的题目:《一个人的中国》。
他伸了个最大限度的懒腰,抻得脊椎骨咔咔响,又扭身将自己抛到床上。
房间外突然传来一记闷闷的关门声,然后涌来一阵嘈杂。
他站起来,溜到房门边,将耳朵贴在门板上,正好听到韩家书扯着喉咙在吼:“川儿,快出来,你老汉儿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