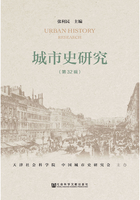
·空间结构与环境变迁·
密州城市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1]
古帅 王尚义
内容提要:密州城最早起源于古东武邑,由古东武邑发展成东武古城,东武古城依东武冈而建,大约至汉代因水源缺乏而迁建于东武冈下,形成后世所称的南城。至北魏永安二年(529)置胶州,在南城基础上扩建北城,奠定了以后密州城的基本轮廓和空间格局。隋开皇五年(585)罢胶州改置密州,无论是在园林建设还是在文化繁荣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苏轼知任密州不仅促进了密州城的建设,而其密州城市水利设想也是留给后人的重要文化遗产。
关键词:东武古城 北魏南北城 密州城 苏轼
城市历史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且相对成熟的分支学科。自侯仁之先生开创现代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以来,一大批历史地理学者加入到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队伍中来,具代表性的有马正林[2]、李孝聪[3]等。对于山东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侯仁之先生对淄博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历史地理考察。[4]顾朝林对山东烟台地区城镇变迁之历史过程进行了研究。[5]李嘎的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半岛城市地理研究——以西汉至元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演变为中心》对山东半岛的城市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6]刘伟国对潍坊地区的城镇体系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7]具体到诸城或者密州的研究,卜正民先生在《为权利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有一章专以诸城为研究对象,对晚明诸城士绅捐助寺庙的活动进行了社会史方面的研究。[8]其他还有不少研究集中在宋代密州区域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9]总的来看,当前还没有文章专门对密州城市的历史地理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密州城市的起源和演变进行初步探索,并对苏轼的密州城市水利设想进行分析。
《太平寰宇记》卷24记载:“……(北魏)永安二年,分青州立胶州,以胶水为名也。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胶州,五年,改胶州为密州,取境中密水为名。”[10]据此可知,密州因密水而得名,上承胶州,虽然在隋唐金元之际密州之名屡有反复,辖境也有所变更,但终于延续了下来,至明初密州才被撤去,诸城县改属青州府管辖。乾隆《诸城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元年夏四月置山东行中书省……(洪武)二年……夏六月戊戌省密州,以诸城县隶青州府,以州治为县治。”[11]也就是说,密州前后延续了近800年的历史,在今天的诸城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密州的前身是胶州,而胶州州治是在东武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要弄清密州城市历史的起源和发展,必须对东武县城的历史地理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探讨以下相关问题:东武县的起源在哪里?为什么会起源于这里?北魏的政区变革给东武的城市空间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唐宋时期的密州城又是什么样子的?正是这些问题牵引着笔者不断地思考与探索。
一 东武城的起源及其地理基础
今天的诸城市“诸城”之名始于隋开皇十八年(598)改东武县为诸城县,《太平寰宇记》记载,诸城之名“取县西三十里汉故诸县城为名”。对于诸城名称的历史溯源笔者已有文章进行分析,[12]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诸城置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的前身就是东武县。东武县大约设于秦末汉初,[13]《水经注》卷26潍水部分记载:“……(潍水)东北过东武县西,县因冈为城,城周三十里。”[14]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复原东武县的一些情况:东武县最早是“因冈为城”的,或可将之称作东武岗。[15]东武岗位于今天诸城市区南部的古城子一带。对于古城子,明万历《诸城县志》有记载:
古城,在今县治城东南门外里许高岗之上,城周约五六里,东北、东南、西南三面城角犹隆然圮而不夷,独西北角一面,尽为两水冲成沟壑,无覆遗址,士人从来称为古城,莫知何成也……窃意此城三代时所筑,其全枕高岗,未知何以,或时遭洪水,民畏下而就高舆,未可知也……则东武之名其来已久,非始于汉初,而此城或为上古东武邑,殆秦汉置郡县,此城或敝隘难居,因于西侧冈下复筑今城,仍袭名。[16]
根据上面的史料记载,我们基本上能够确定东武城的起源了。最早的东武城就是建在东武岗上,当地人称之为古城(或古城子),城周长五六里,至明万历时仍能看到古东武城倾圮的遗迹,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东武古城。至于郦道元《水经注》所记载的“城周三十里”恐不只是指后世所说的南城,很可能还包括东武古城在内。先人们为什么放弃高岗之上的古城而移至岗下另筑新城呢?上面的记载基本上给出了答案:其一缘于洪水的冲击,其二是“敝隘难居”。古人一方面需要躲避洪水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远离水源,以前大部分城市最初的选址多在水边的高地,古东武城也不例外。[17]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东武古城就显得“敝隘难居”,不得不在东武古城西侧的岗下另筑新城。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需要谨慎下定论,东武岗可以说是今天诸城市区海拔的最高点,在这里建城受到洪水威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笔者认为,人口随着社会的稳定而增多,却导致取水困难和“敝隘难居”,这是古东武城迁变的主要原因。[18]
如果继续追问东武古城的源头,正如明代士绅所推测,或许可以认为它源自明人所说“上古东武邑”,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齐道里记》云:“东武县本有东武山……今犹有东武里。”[19]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东武县源自东武邑、东武里,而“东武”之名还可追溯至东武山,这恐怕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了。
确定了东武古城的起源,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其所处的地理环境。诸城市位于山东半岛的南部,泰沂山脉与胶莱平原的交界处,处胶莱平原南部的潍河平原,地势南高北低,东南部为起伏较大的低山丘陵,县境中部向北系一片波状平原,在南高北低的地形控制之下,境内河流多由南向北流,潍河为境内的最大河流,自西南而东北贯穿全境。潍河在境内支流众多,组成叶脉状水系。[20]《水经注》记载:
(潍水)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东北流注潍……潍水又北,右合卢水,即久台水也。水出琅琊横县故山,王莽之令丘也。山在东武县故城东南,世谓之卢山也。[21]
这里提到的“扶淇之水”即今天的扶淇河,久台水、卢水就是今天的芦河,它们都发源于东南部的山区,流向西北注入潍河。东武古城就位于芦河和扶淇河之间的东武岗上,或者说东武岗就是一个分水岭,当然,在这里选址建城所起的防止洪灾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诸城地处季风气候区,降水多集中在夏季,每遇大雨,众多支流汇入潍河,难免会有洪灾发生。再加上境内潍河水系河床比较大,水流湍急,侵蚀力强,河道弯曲,宽窄不一,行洪能力差,洪灾也就更易发生。当然,如前所述,东武古城由于处在至高的地理位置上,受到洪灾的威胁几乎没有,但是后来的东武城就难逃此劫了。

图1 诸城水系与诸城城址略图
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明正德)八年(1513),秋大雨,潍水逆流,壅扶淇水入城门,坏庐舍无算,修城。”[22]这样的水灾在诸城的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所谓的“潍水逆流”也就是由于河道的行洪能力差导致潍河及其支流合流之水倒灌而冲坏县城。虽然这是发生在明代的事情,但洪灾对城池的毁坏也可见一斑,前文所引明万历《诸城县志》中记载的“独西北角一面,尽为两水冲成沟壑”中的“两水”很可能就是这里提及的潍河及其支流扶淇河,而其冲击的“西北角一面”则恐被误指为东武古城的西北角,实际上当是后世迁建于顺东武岗自南而北的缓坡之上的东武城。当然,通过这点,我们也就更能加深对东武古城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特征的认识了。
二 秦汉时期的东武城
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古城在县东南门外冈上……《齐乘》以今南城为汉县或汉复迁筑者。”[23]其中所引《齐乘》的这种看法还是比较严谨的,也是较为科学准确的。又苏轼在《山堂铭》“序言”中提到:“熙宁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来告,故东武城中沟渎圮坏,出乱石无数。”[24]乾隆《诸城县志》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故东武城)若为今南城,不当云野人来告也。”[25]显然,这种解释是正确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明代仍能看到东武古城倾圮的遗迹,更何况是在宋代,苏轼亦曾于此“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26]清乾隆《诸城县志》对东武古城进一步描述:“城址存者,高阔不减今城。城东南有将台,台南多土堆如营垒状,大者一,小者六,古城演武所也。”[27]根据以上史料记载,我们又能加深对东武古城的认识,但是,至于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又是什么时候迁移至东武岗下的,到目前为止还很难弄清楚,不过从秦汉时期东武政区的历史沿革,再结合现代的考古发掘,或许能揭开东武古城的奥秘。
我们先从方志记载看秦汉之际东武的情形。明万历《诸城县志》记载:“东武国:即汉东武县,今县南城,以封建王侯谓之国,以统属县邑谓之郡。东武先为县,次为国,次为郡。”[28]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高祖六年封郭蒙为东武侯,传子它,至景帝六年方除国。”[29]又记载:“琅琊,齐邑……汉置琅琊县……勾践徙都琅琊。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以为郡……汉高帝吕后七年以为王国,文帝三年更名为郡,王莽改曰填夷。据此,则琅琊王泽实国于此,同时东武侯郭它固国于东武也,而汉书地理志琅琊郡五十一县首东武,琅琊县下亦不著王国,岂泽徙燕之后国废,郡治遂迁东武也。”[30]
秦汉之际,社会动荡,汉代汲取秦朝兴郡县制之教训,实行郡县和郡国并行制,又遇吕后执政和新莽改制,政区变迁较为繁复。如果按照明万历《诸城县志》所说的“东武国,即汉东武县,今县南城”的话,那么东武古城的筑城肯定在汉代之前。虽然我们未能找到直接影响东武古城城址迁移的相关史料,但是从政区繁复演变背景下,加之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我们或可从侧面看到那个时代留在东武古城身上的烙印。
表1 秦汉时期琅琊地区的战乱和灾害事件

此外,从现代的考古发掘来看,东武古城城址夯土层次分明,遍地残瓦遗留,并多次出土篆文“千秋万岁”瓦当,残存柱基,石佛、菩萨等神像,以及五铢铜钱、铜镞、龟纽铜印、铁鼎、铁镢、镰刀等亦多有发现,城西侧出土的残石佛、菩萨石像,雕刻精致,形象逼真,有些还涂有彩铁金,鲜艳如新。[31]如此丰富的遗存不仅反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力状况,还能看出佛教在琅琊地区的兴盛。东武古城历经战国至两汉,先后为琅琊国国都、东武侯国都,以及琅琊郡治所,并发展成为东南海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地。
三 魏晋时期的南城和北城
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东武在汉为琅琊郡治时,兼设者数县,诸其一耳。后汉章帝时琅琊孝王徙国开阳而郡随之是地,兼设之县遂有属北海国者,曹魏郡县无可考,晋宋间诸、东武或属城阳,或属东莞,或属平昌,不复属琅琊矣。”[32]这里所说的东武在汉为琅琊郡治,应该是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置刺史部十三州而琅琊郡属徐州时的事情,而“兼设者数县”则要追溯至汉初吕后执政的时候。很明显,到了曹魏以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琅琊地区的政区变更更为复杂,而东武的琅琊郡治的地位也不复存在,东武古城至此时也早已由东武岗上迁至岗下了。
在诸城的城市发展史上,北魏永安二年(529)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州理中城,后魏庄帝永安二年筑以置胶州。”[33]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后魏)庄帝永安二年置胶州于东武县,筑北城为州治,领郡三。”[34]所谓的“领郡三”即“曰东武者治姑幕,所领扶淇、梁乡皆今县境;曰高密者治高密,平昌、东武属焉。”[35]又记载:“城分南城北城,《齐乘》密州理有中外二城。”[36]“中外二城”,即表明北城和南城的格局至此初步形成。
北魏在南城北面另筑北城,实际上也就为唐宋时期的密州城和明清民国时期的诸城县城奠定了基础,前后延续了1400多年。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城周九里有三十步,高二丈有七尺,阔三丈有六尺,南城视北城广增十之二,袤增十之五。城门五,南曰永安,东南曰镇海,西南曰政清,东北曰东武,西北曰西宁。有月城,有重门,有楼池深一丈有五尺,阔三丈。”[37]虽然这已是明初以来多次重建后的诸城县城,但是史志记载的数据与现代考古调查测量的结果基本相似,[38]这样的规模应该与魏晋时期南北二城和唐宋时期密州城的规模相差无多。此外,从城市的轮廓结构来看,南城宽而北城窄,这样整个州城就好像一个“凸”字,而贯穿南北城正中间的大道则成了整个城市的中轴线。
又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南北城之交有门曰双门,故东武门址也,其左右城垣,前志以为后魏置胶州时撤之,合南北为一城。”[39]据此可知,北魏置胶州时,把原秦汉以来的东武城(即南城)的北城门、东武门两侧的城墙拆除了,而保留下来了东武门,后又改名为双门,这样看来,双门的由来就要追溯到北魏扩建北城的时候了。
四 唐宋时期的密州城
1.密州城的空间结构
隋朝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全国的政区也做了一番调整,东武的政区变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诸城县……后汉属琅琊国,晋属东莞郡,后魏属高密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属胶州,五年,改胶州为密州,县仍属焉。十八年改东武为诸城县。”[40]自此,诸城迎来了发展史上的“密州时代”,以后历经唐宋金元,虽然密州名称屡有反复,归属上随朝代的更替也多次易手,但是东武县作为密州的州治,基本上保持稳定,还是保持在州这一较高的层次上。
密州城是北魏南北城的延续和发展,依然保持着南北二城“凸”字形的轮廓,自州治正门向南至永安门中贯的府前大街仍然是整个城市的中轴线。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隋开皇十八年始改东武为诸城,立县治为密州倚郭……明初,省密州,即州治为诸城县治,而南城之县治遂废。”[41]唐宋至明初的密州城在继承北魏南北城的基础上,以北城为州治,而南城为诸城县治。我们可以再转换一下思维,既然唐宋密州城是在北魏南北二城的基础上承继过来的,那么魏晋时期的南北二城大致也应是这样,北城为胶州州治,而南城为东武县治所在。
至宋代,自州治至永安门的南北中轴线就更为凸显了,乾隆《诸城县志》记载:“街巷自县治南抵永安门(南门)曰大街,苏轼所谓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也。”[42]查苏轼《盖公堂记》:“治新寝于黄堂之北,易其弊漏,达其壅蔽,重门洞开,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名之曰盖公堂,时从宾客僚吏游息其间。”[43]此处所说“黄堂”,即为知州办公之处,盖公堂建成之后,“重门洞开”,南北相望才如引绳,中轴线至此才能说是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南北贯通。

图2 苏轼知密州时期的密州城想象略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城内的交通状况。明初撤密州后改诸城县隶属青州,南城的县治功能亦随之被废弃而改为军城,北城州治作为县治为民城。唐宋以来的密州城历经明清多次重修,但多是局部的修整或者是城郭范围的稍扩,城内的道路走向变化不大,至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增修、二十八年落成之后,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和布局也就稳定下来。
经过乾隆年间重修过的诸城县城城门有五:“南曰永安,东南曰镇海,西南曰政清,东北曰东武,西北曰西宁。”[44]乾隆《诸城县志》记载:“自县治(即原密州州治)南抵永安门曰大街……县治前自东武门抵西宁门横街东曰东市(街),西曰西市(街),人迹骈阗居一城之最……自镇海门抵政清门,中穿大街曰郭街,旧名四牌楼郭街。”[45]自此,诸城县城内主干道路的格局就清楚了,只不过县治门前的东西市街为全城内人口最为密集的场所,一则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条商业街,二则与密州撤治后的城市功能分区不同而引起的城内人口分布不均有关,至于唐宋时期的密州城是否如此,笔者推测恐怕不如明清时期的“东西市街”繁忙。
值得注意的是,清乾隆《诸城县志》对明代以前的诸城县治所在提出了一种怀疑,有记载说:“由仓湾而南者曰后营,旧为军城时,兵营巷东为所院,旧千户所也,前志云千户所旧基为天清观,疑即诸城县故治。”[46]其中所说的“前志”当是康熙《诸城县志》,如果上述推疑成立的话,我们也就能确定唐宋以降的诸城县治的位置了,这也反映出密州城内部结构变迁的复杂性。
2.苏轼与密州城的亭台园景
苏轼知密州期间除了修建盖公堂,还修建了山堂、西园、超然台等景点。苏轼《山堂铭》序文中记载:“故东武城中沟渎圮坏,出乱石无数。取而储之,因守居之北墉为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开新堂北向,以游心寓意焉。”[47]北墉即为密州城的北墙,大意为苏轼把东武古城遗址取来的“乱石”在州城北墙堆成五座小山,在上面种树,并在州治大堂开北门,北墉之山景随时可见,虽客寓他乡,但也增添了不少乐趣。
西园,也叫使园。苏轼《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一文中,后人注解说:“超然台在使园之北,先生有记云:使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48]据此可知,西园当在密州州治的西侧,超然台的南面,注解中所提到的“记”应为苏轼《超然台记》,其中说道:“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49]这里所说的“园”当是指西园,苏轼来到密州后,伐取了安丘、高密等地的林木,不仅修葺了州治庭宇,修建亭台,而且建造园圃,密州城为之焕然一新。另苏轼有《春步西园见寄》云:“岁岁开园成故事,年年行乐不辜春。”后有查注云:“宋制,州守每岁二月开园,散父老酒食。”[50]据此可知,园圃的修建是州守的职责所在,苏轼在履行职责的同时,更为密州城撰著了不少奇文佳句和增添了笑语欢歌。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尝以轼诗文考之,其时,署西北有园……园曰西园……园之斋曰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其轩曰西轩。”可见,西园还建有西斋、西轩,苏轼在这里“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宴请宾客,其乐融融。当然,当时的密州城不止一座园圃,苏轼还有《见邸家园[51]留题》和《再观邸园留题》诗二首。邸园应该也是密州地区的名园,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邸家园又见轼诗,今县东南七十里有邨名邸家河,邸氏犹族居焉,其园主之苗裔也。”[52]清人所说的“(苏)轼诗”应该是前面的两首,如其所说确实,则不但能从中看出密州城的园亭之美,更反映出私家园林的兴盛,我们或可从邸园“小园香雾晓蒙蒙”[53]的景象之中去体会昔日密州的盛景雅境。
宋代密州城最引人注目的亭台要数超然台了,超然台位于州治的西北面,苏轼所言“因城以为台”,也就是说超然台位于北墙之中,是借助北城墙而建筑的。既然是“稍葺而新之”,这就说明超然台早就存在了,至于到底什么时候建成,不得而知。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北城上与超然台东西并峙者为北极台。”超然、北极二台并峙的局面至明嘉靖年间尚存,而北极台至清代倾圮废弃。回过头来再看看超然台的重新落成,站在超然台上看,“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54]更开阔了视野,再加之“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55]自然也就成了文人墨客畅述幽情的理想场所,苏轼有《望江南》诗云:“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56]虽然诗文中多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密州的景象,这里所说的“半壕春水”很可能就是密州城池之水,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密州城另一个重要园亭水景——沧湾。
沧湾,又名沧浪湾,位于今诸城市区电影院的西南,市图书馆北面,和平大街的东侧。从沧湾的位置来看,地势较为低洼,南城之雨水顺着自东南向西北倾斜的缓坡而流,多汇集于此。至于沧湾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已很难考定。据诸城地方史研究专家任日新先生考证,沧湾很可能是在汉魏之间修建南城和扩建北城之时就地取土而成。[57]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沧湾也就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
上面这些亭台园圃当然只是密州城景观之一瞥,还有很多我们已经很难考证它们的确切位置,像快哉亭、流杯亭等,苏轼或于此送别故人,或于此聚友赋诗给密州,甚至在此给全世界的文人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妙章佳句和千古绝唱。
五 结语
如果把古东武邑看作密州城的历史起源,至明初撤密州为诸城县,则密州城有两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它历经两汉迁建于东武岗下而成南城,后又经过北魏永安年间的北城扩建,最终奠定了密州城的城市形态和基本格局。密州在诸城发展史上前后延续了近800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可以说都达到了诸城发展史上的新高峰,苏轼知任密州时修葺庭宇,建盖公堂、西园,修筑超然台,祈雨常山,凿雩泉、建雩泉亭,修筑扶淇堤堰,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文化的气息。至今,“密州”之名也有1430年[58]的历史了,虽然密州早已于明初撤去,但“至今东鲁遗风在”,我们仍能从今日诸城之密州街道、密州路、密州宾馆等名称中看出人们对昔日密州的那份向往和追忆。
致谢:笔者在山东诸城市实地考察的过程中,诸城市超然台管理处乔云峰先生和诸城市地方文化研究会王桂杰先生提供了不少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古帅,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王尚义,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
[1]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325)、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0320)资助成果。
[2]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3]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4]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336~388页。
[5] 顾朝林:《山东烟台地区城镇历史发展研究》,《历史地理》1990年第7辑。
[6] 李嘎:《山东半岛城市地理研究——以西汉至元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演变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相关文章有氏著《青州城历史城市地理的初步研究——以广县城与广固城为研究重心》,《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青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步研究》,《历史地理》2010年第24辑;《从青州到济南:宋至明初山东半岛中心城市转移研究——一项城市比较视角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南北朝时期济南城市变迁考论——基于城市行政等级与职能作用的考察》,《史林》2011年第2期;《潍县城:晚清民国时期一个区域性大都会的城市地域结构(1904~1937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7] 刘伟国:《山东潍坊地区区域城镇体系发展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8] 〔加〕卜正民:《为权利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241~263页。
[9] 贾茜:《北宋密州区域经济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卢厚杰:《北宋密州地区人才崛起探因》,《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张蕾蕾:《密州板桥镇港口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0]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4《河南道·密州》。
[11] 乾隆《诸城县志》总纪2第1《总纪上》。
[12] 古帅等:《诸城地名的历史溯源》,《中国地名》2014年第4期。
[13]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8,第630页。
[14] 对于东武置县的问题,笔者在《诸城沿革地理研究二题》(未刊稿)一文中进行了分析,拙文认为东武设县的时间最晚在汉高祖六年(前201)至吕后七年(前181)间,较为准确的时间应是在秦灭齐置琅琊郡(前221)至郭蒙被封东武贞侯(前201)间。
[15] 这里的“冈”准确地说应为“岗”,下文除引文需尊重原文外,统一用“岗”。
[16] 万历《诸城县志》卷8《古迹》。
[17] 李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半岛城市地理研究——以西汉至元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演变为中心》中考察了潍河流域的城市选址,认为大多是选址于潍河支流附近的高地上。
[18] 据笔者对诸城市博物馆韩岗先生的访问,东武古城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深井(大致是这个意思),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古城人们饮水困难的问题,笔者对此也表示赞同。
[19] 《太平寰宇记》卷24《河南道·密州》。
[20] 诸城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印《诸城县概况》,1984,第3~4页。
[21]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630页。
[22] 乾隆《诸城县志》总纪2第1《总纪上》。
[23]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5《古迹考》。
[24] 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齐鲁书社,1995,第263页。
[25]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5《古迹考》。
[26] 苏轼《后杞菊赋》,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236页。
[27]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5《古迹考》。
[28] 万历《诸城县志》卷8《古迹》。
[29] 乾隆《诸城县志》表11第2《封建表》。
[30]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5《古迹考》。
[31] 任日新:《东武故城》,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635~638页。
[32] 乾隆《诸城县志》表11第2《封建表》。
[33] 《太平寰宇记》卷24《河南道·密州》。
[34] 乾隆《诸城县志》总纪2第1《总纪上》。
[35] 乾隆《诸城县志》表11第2《封建表》。
[36]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4《建置考》。
[37]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4《建置考》。
[38] 韩岗:《密州故城》,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632页。
[39]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4《建置考》。
[40] 《太平寰宇记》卷24《河南道·密州》。
[41]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4《建置考》。
[42]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4《建置考》。
[43] 苏轼:《盖公堂记》,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247页。
[44]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4《建置考》。
[45]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4《建置考》。
[46]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4《建置考》。
[47] 苏轼:《山堂铭》,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263页。
[48] 苏轼:《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363页。
[49] 苏轼:《超然台记》,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250页。
[50] 苏轼:《春步西园见寄》,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365页。
[51] 邸家园,又称邸园。
[52] 乾隆《诸城县志》考12第5《古迹考》。
[53] 苏轼:《再观邸园留题》,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367页。
[54] 苏轼:《江城子》,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359页。
[55] 苏轼:《超然台记》,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250页。
[56] 苏轼:《望江南》,转引自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350页。
[57] 任日新:《沧湾小考》,诸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编《诸城文史资料》第11辑,1990。
[58] 从隋开皇五年(585)改胶州为密州至今(2015)已有1430年,而至明初省密州,密州作为实在的行政区划则存在了近8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