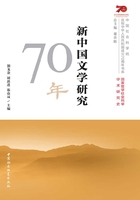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文艺任务与文艺建设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3月,来自华北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齐聚北平,商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的筹备事宜。对于即将召开的大会,筹备会主任郭沫若明确指出它的目的:“举行这一个空前盛大与空前团结的大会,主要目的便是要总结我们彼此的经验,交换我们彼此的意见,接受我们彼此的批评,砥砺我们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1]当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文代会”上的三个报告,茅盾的《在反对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介绍了国统区的文艺经验,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论述了解放区的文艺经验,郭沫若的《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则提出了文艺工作新形势下的新目标。郭沫若的话以及这三个代表性报告,都反映出当时文化界所存在的区域性和文艺队伍之间的区别与分野,而这种区别与分野的弥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亟须解决的文艺任务。
具体说来,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主要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在战争以及两军对峙时期,分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一直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前者的服务对象是解放区的人民大众和人民军队,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相关内容;而后者面对的不仅有国统区的普通百姓,还有站在进步对立面的旧势力和反动势力,因此他们的主要任务则是暴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启蒙广大民众,主导方针除了传到国统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还有“五四”以来的启蒙立场及其思想武器。这是两条战线,两种经验。随着全国的解放,两条战线上的战友实现会师。然而,这种会师并不意味着消除或解决了二者在文化立场和文艺经验方面的原有分歧。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这一目标看起来明确,但结合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文艺经验看,却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诠释。几年之后,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表现出来的困惑,正是这种分歧的体现。
应该说,从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与召开开始,解决这种分歧,统一和改造文艺界思想意识的工作就已经拉开了大幕。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其一,建立制度,将所有文艺工作者都纳入国家管理范围。在“文代会”召开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出了全国委员会,制定了章程。相继成立的组织还有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等。1949年9月,曾在“文代会”期间试版的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正式创刊。资料显示,从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到年底,“全国各省、市成立了四十个地方文联或文联的筹备机构,出版了四十种文艺刊物”[2]。这些机构都有一定行政级别,相关负责人也享受相应行政待遇。这种方式将文艺工作者全部纳入体制之内。其二,组织知识界参加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其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活动并不限于知识界,还包括工商业从业者等,但主要是知识界。进行思想改造,有一个总的逻辑前提,即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进入新社会,人们不能够再留有旧社会的思想痕迹。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本质性变化,人们自然应该调整其观念,使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由此来看,这一改造是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其三,通过一系列文艺界的争鸣与批判,文艺工作者逐渐熟悉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始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工作者逐渐熟悉了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意图和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三大文艺批判运动,即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评论》、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以及“胡风案”。实际上,这种争鸣与批判早在《武训传》的批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这些争鸣比较温和,形成了非常活泼生动的论争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文艺政策与文艺发展状况为接下来文艺界展开的“美学大讨论”定下基调,是讨论也是批判,是文艺或美学论题也是政治问题。“美学大讨论”晚于三大文艺批判运动,但它兴起时,三大文艺批判方兴未艾,其他文艺批判有的也在进行之中,因此,它们彼此间形成一种呼应,构成了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文艺与美学的整体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