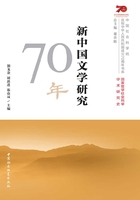
第二节 关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文艺理论的热门话题。在长达数年的研究与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是钱中文、陶东风、杨春时、周宪、金元浦等人的文章。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现代性的两个问题》一文中,着重讨论了“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与现代性”和“现代性与文学理论人文精神问题”。他指出:“在文学理论中,探讨现代性问题,自然不能把它与科学、人道、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及其历史精神、整体指向等同起来,但是又不能与之分离开来。文学理论要求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从合乎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我以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
杨春时、宋剑华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1996)一文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杨春时认为,现代性问题是国内外哲学、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文学思想界并未重视这个问题。这次讨论不但弄清了现代性的含义,而且进一步探讨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陈剑晖的《现代性:百年文学的艰难历程》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常常呈现出近现代交叉复合的文学状态。杨义的《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世纪反省》则预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21世纪的追求,具有20世纪初级阶段的诸多不同特点,即追求平等和深入的开放性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阐释和转化。
文学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地酝酿了其“自反性”的方方面面,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博弈在哲学、美学和诗学方面都有极为丰富的表现。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文学现代性的策动,促进了文学中的政治群体意识的解体,审美意识的激变,使文学与文学理论初步获得了自主性与独立性,开始回到自身。这一过程正是文学观念走向开放、对话、多元,走向现代意识的过程。有论者认为,现代性与文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促使文论科学化,使其进一步走向自身,关注自身的学理,从而解决文论的“自主性”问题;推动文论民主化,使其自身的理论思维走向多元与对话;实现文论理性化,使之改造和重建而更富有人文精神。[7]
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学者们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如陶东风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不是新的中国民族身份生成的过程,相反是一个“民族身份彻底丧失”的过程。吴兴明认为,现代性是构成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体制乃至现实生活的世纪性母题。对现代现象的激烈反应——拿来、拒斥、设想、忧虑、方案选择、反驳等,具体化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不断震荡、扩散、变形、演变的学术文化景观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经验,而各种思潮、主义、知识主张等,又构成极为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知识谱系。为此,要恰当地清理20世纪中国文论,首先要对之进行现代性的整体审视。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至少体现为如下层面:文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先锋性植入;理论—文学语言的西语化;文学经验的模造性;理论批评生产体制的现代建制。此外,吴予敏的《美学与现代性》、周宪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耿传明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起源》、柯玲的《汪曾祺创作的现代意识》、涂险峰的《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现代性终结”话语质疑》、马相武的《面对变迁:文学提升与现代人文性》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展开了研究或探讨,为这次讨论直接或间接地增添了色彩。
正如钱中文所言,现代性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
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理探讨既是科学的,同时也应当是充满人文精神的。近百年来,文学理论倾向于文学自身内在的、本体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削弱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在我们充分注意并研究文学的种种形式因素的同时,需要张扬文学的人文精神,呼吁人的血性与良知、怜悯与同情。总之,我们面临着对文学理论现代性的选择,同时我们也将被现代性所选择。
当前,社会变革处于无序状态,文学也混杂不清,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纠缠在一起,人们似乎失去了方向感,也失去了思想追求,在这种形势下,文学理论也无所适从,失去了推动力。杨春时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立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设,而不是以解构来代替建构。对后现代理论的借鉴,必须为现代性建设服务,以后现代理论的合理因素消解现代性的偏执,通过这种解毒过程,建立健全的现代性文论。如此,21世纪中国文论才是有可为的。
总之,文艺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在“阐释的焦虑”中爆发出大量“焦虑的阐释”。如金元浦强调的中西文论相向而行的“非同步现象”、周星提出的中国电影现代性历程所反映的“文艺矛盾”、刘毓庆说的“寻找文学的价值重心”、代迅的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内在机制”、董国炎指出的“群体的、宗法的深层价值观念对现代性的制约”、俞兆平探讨的科学主义与“五四”新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傅道彬论述的“文化英雄的终结和平民文艺的登场”、孙绍先提出的“全球化的趋势下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问题”、陆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现代文化所作的透视与分析、彭富春对中国现代性话语进行的解剖,以及他提出的“走出传统,又走出西方,建立中国的现代性”等,都是有关“文艺理论现代性”这一“旧话题”中的“新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