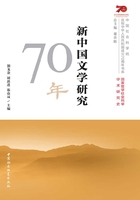
第二节 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学科化进程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内政治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进新时期。80年代开始,知识界开始批判极“左”话语,随着僵化刻板思维的打破,学术研究领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西学再次涌进,中外文化交流也以空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得以发展。各种理论和文艺思潮被大规模译介,中国社会迎来“新启蒙”。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以跨文化沟通为主旨的学科,既获得了发展的可能性,其研究的必要性也凸显出来。因此,1978—2000年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段,在这十二年间,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从复兴走向繁荣,并完成学科化进程,成长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独立的二级学科。
一 学科复兴之旅的开启
新时期以来,国内和国际环境共同造就的有利外部条件,与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形成合力,促成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复兴。1979年9月《民间文学》杂志率先发表了刘守华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作者后来还著有《比较故事学》[2]《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3]等相关著作。虽然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主张“比较”研究,但这些提法也开了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先声。复兴之路的真正标志是钱锺书先生的巨著《管锥编》(于1979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管锥编》接续了20世纪前半期个人化的、零星开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即一些学术大家以自身深厚的中西学养为基础,在自觉的跨文化视野中探求文学普遍规律;同时,该著作也是非学科化时代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所臻达的高峰之一。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面对应着这样一幅图景:夜空中几颗星辰璀璨明亮,但只有寥寥数颗且彼此孤立,尚未形成群星灿烂的星系。那么,这种局面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彻底发生了变化。在此期间,中国比较文学全面复兴,并且完成了学科化过程。
二 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化进程
在现代学科化建制中,学科化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学科化不仅意味着研究者内部形成自我认同并获得学界普遍承认,对于集结科研力量、培养后继人才意义重大,为本领域研究的良性发展提供必要条件,更重要的在于,顺利和蓬勃的学科化进程,本身就是对一个时代繁荣发展的表征和印证。重要的是,只有良好的社会条件与学术土壤,才能让一个学科快速进行自我完善。
据统计,自1983年国家教委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正式设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以来,三十多年来,比较文学教研队伍不断壮大、教学发展迅猛。目前全国各地已有一百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有一百多所高校拥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二十七所高校拥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下文从四大方面来概括这条从复兴走向繁荣之路,这也是其学科化的步步历程。
(一)学科意识树立与井喷状研究
在1978—1980年的研究刊物上,出现了许多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例如季羡林的《泰戈尔在中国》[4],林秀清、阎吉达的《卢梭、伏尔泰在中国》[5],戈宝权的《郭沫若著作在日本》[6],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7],乐黛云的《尼采与现代中国文学》[8]等。这些研究采用了比较文学中经典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范式,或考察中外各作家、作品、流派、风格间的影响、接受、转化、再生长等诸种关系,或比较不同民族、语言、国别间作品和文学现象之异同。同时,也有若干文章,如温儒敏的《美国两教授谈比较文学》[9]、赵毅衡的《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10]、谢天振的《漫谈比较文学》[11]等,介绍了当时国际上的比较文学研究现状,并明确倡议在中国建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比较文学。
经过几年的积累和酝酿,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文学研究界对比较文学的概念已经有了较为清晰和准确的把握。学者们普遍意识到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独立于国别文学研究的必要性。1981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它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学术团体。随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一方面翻译介绍国外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和发展动态;另一方面推出本土学者的探索成果,如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1982)、基亚的《比较文学》(1983)等,在当时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的传播。
在这段时期,既有老一辈知名学者如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等人的积极倡导,又有一大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人热情投入其中,比较文学研究很快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在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前后,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比较文学相关论文数量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仅1984年上半年的论文数量就占到了过去五年间发表论文总量的一半。[12]此后,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到2000年前后,每年出版专著几十种,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专业论文达数千篇。根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13]一书所作的统计,在二十年间,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刊载的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总计一万两千余篇,出版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三百六十多部。从成果数量上看,比较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学科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化过程的一大特点,就是始终伴随着明确的学科意识,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对学科理论的高度关注上。关于“中国比较文学”概念的内涵、基本理念、学术特色、研究范式、发展方向等学科基本问题的讨论一直具有极高热度,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新挑战的出现而不断展开更加深入与多维的探讨。
“中国比较文学”这一组合词的两个组成部分恰好代表了学科理论探讨的两大焦点。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危机意识便始终伴随,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派对传统法国学派的批判,到80年代关于比较文学“理论化”问题的争论,再到20世纪末对泛文化与全球化挑战的回应,比较文学在一次次争论和辨析中,完成学科理念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方向的调整。
一方面,中国比较文学界借助“后见之明”,对较早时期的争论,如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事实联系与审美价值、理论探讨与作品分析、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采取辩证调和的理性态度,兼容并蓄,并结合本土古典文化资源提出“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围绕困扰学科已久的“可比性”问题展开持续讨论。另一方面,面对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愈加迅猛的全球化趋势,中国学者以积极姿态投入国际比较文学学界对学科定位的再思考,希冀在多元文明交锋与学科整合加速的全新时代语境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聚焦于“比较文学”的探讨,体现了基于学科性质的全球视野和主动参与国际对话的学术自信;那么,对“中国”的关注则对应着一门舶来学科在本土环境中生根成长的过程。早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筹备组于1982年召开的“西安座谈会”上,就有学者提出“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中国学派”。对“中国学派”的倡导肇始于港台学者,围绕它的讨论一度成为比较文学在大陆复兴时期学界关注的中心,因为其实质即为中国比较文学如何自我定位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派”的提法热度渐减,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化探讨的结束,相反,这说明学者不再热衷于树立旗号,而是更加冷静和深入地思考“中国”定位的深层次内涵。“中国”不仅仅牵涉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源的本土化,更重要的是,如何生发出植根于自身文化发展脉络的问题意识,以及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模式才能与国际学界有效交流。
(三)高校科研教学体系的建立与教材的编写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以一种成规模、有建制的发展模式成长起来,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科研教学体制便是学科发展的基本依托,它保证了科研力量的集结、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不同研究流派特色的形成。
1993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培养高端学术人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文学一级学科隶属的二级学科,进入国家认定的专业和课程教学体制。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随后纷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成立硕士、博士培养点。2000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设立比较文学系,成为第一所招收比较文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国内高校。从本科教育、博士生培养到博士后流动站建设的系统而连贯的人才培育体系完全形成。培养学生的需求促进了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主编的《比较文学导论》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时至2000年,已有几十种教材出版,基本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自学者研读的需要。除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化进程还体现在学会组织的创立和专业刊物的发行。
学界普遍将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正式成立,视为中国比较文学全面复兴的标志性事件。学会由国内三十六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是当时全国研究力量的一次总集结。作为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为领导与协调学界工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有力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学会成立之后,每隔三年举办一次高水平学术年会,至2017年,已成功举办十二届。学会下属的各研究领域与各地方的二级学会也纷纷成立,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我国第一家比较文学刊物《中国比较文学》于1985年创刊,成为集中发表本学科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阵地,并及时刊发中外比较学界研究和出版的最新动态和信息。自从1996年改为季刊以来,刊物容量增大、栏目更为齐备,关注学界前沿问题和理论探讨是其特点。另外,国内一些高校也主办了比较文学刊物,如《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比较文学研究》《文贝》《跨文化对话》等。
(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成熟
在学科化过程中,中国比较文学也逐渐形成以“跨越”和“沟通”为基本界定,以“和而不同”为基本理念,同时又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学科体系,形成文学关系研究、译介学、比较诗学、形象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学人类学、海外汉学等十余种研究分支,以下介绍其中研究力量较为雄厚、讨论热度较高、学术特色比较鲜明的几种。
跨文化文学关系研究:近代以来,外国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苏俄文学以及日本文学对中国作家、作品、文体、写作风格、文学流派影响巨大。若不追溯外来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方式,就无法恰当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面貌和文学品格,这类确实存在的事实联系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中国现代文学也因此成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多以某个作家、作品为个案,追本溯源地考证其接受外来影响的路径,并追寻文学关系事实背后的文化动因。另外,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文化交流,探究各民族文学间的互动关系,同样也是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结合,遂成为我国跨文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大特色。在20世纪末的约二十年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亮点之一,是对于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凸显出来。由于中国与日本同处汉字文化圈,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文化史以各种方式纠缠在一起,因此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必然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内容。1987年,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作为“比较文学丛书”的一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0年,程麻的《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孟庆枢主编的《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刘立善的《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张福贵、靳丛林合著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专著研究的范围涵盖了近代与现代,既有宏观研究也有个案分析,全面深化了对于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的理解,丰富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内涵。
译介学:译介学是专门针对作为两种文化交流中介的翻译文学及翻译现象的研究。译介学之所以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来说具有特别意义,主要是由于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在欧美文学界尚不十分突出的翻译问题重要性凸显。本时期的译介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译介理论探讨和翻译文学个案分析两方面,前者对“创造性叛逆”“误译”“归化”等核心概念多有分析,并集中探讨了“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后者则将译作、译者和翻译行为置于两种文化与社会的背景下,具体分析在翻译这种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理解、交融或者误解、扭曲现象。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堪称这一时期译介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回顾与梳理了中西翻译史上的文学传统,探讨了译介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与相关理论问题,并基于20世纪翻译研究的趋向对翻译文学未来的地位进行了合理预测。
比较诗学:比较诗学是另一个在中国比较文学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研究领域。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均以其作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曾经在学界引起过广泛讨论的一些问题也属于比较诗学,例如,中西文学基本概念的比较、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性转换、传统诗学阐释学的现代意义、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失语症”问题,等等。比较诗学在中国比较文学体系中备受重视,一方面与中国比较文学特别注重理论的研究倾向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如下事实,即中西方诗学都具有悠久传统与丰富遗产,而双方文艺理论体系在思维方式、审美意趣、话语表达等诸方面差异巨大,深层次沟通困难重重。比较诗学研究以中西诗学的跨文化对话为主要探讨对象,具体涉及中国古代诗学概念的意义追溯与现代阐释、中西诗学话语的互译与接受、总体性诗学的建构等各方面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在比较文学界,而且在当时的整个思想人文研究领域都颇有影响。如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1994),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1997),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1999),饶芃子等的《中西比较文艺学》(1999),钱中文等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1997)等著作均引发了广泛讨论。
文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是中国比较文学体系中“跨学科”研究的代表性领域。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该丛书结合文本材料、考古资料,重新解读若干中国上古经典著作,如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1996),萧兵、叶舒宪的《老子的文化解读》(1994),王子今的《史记的文化发掘》(1997),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1997)等著作,屡发新见,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