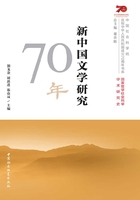
第四节 走向知行合一——民间文学研究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参与
民间文学研究同社会生活实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这门学科自诞生之初,就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为高扬“民主” “科学”大旗,为重建民族精神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也为延安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大批民间文学研究者更是借助自己的理论和知识储备,通过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不同体裁民间文学中特定内容的采录、整理和改编,直接参与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新文化的建设当中。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要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1年编纂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75]。这部发行极其广泛的专题故事集,对破除迷信思想、普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民间文学学科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发展取向上取得的突出成就。
这种取向,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普遍开展,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以保护面临损坏、破坏乃至消失等严重威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为主要宗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兴起伊始就得到了中国的积极支持和参与。由于各国民间文学工作者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很多都涉及对民间文学传统资料的记录、保存,本身即属于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其理论和方法与非遗保护具有很大的重合度。而事实上,在非遗保护工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研究者在理念、思路和方法上为其提供了大量基本的支持。数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从多个方面深度参与到这项活动的实践当中,为它的丰富和发展贡献了诸多来自本学科的智慧;[76]与此同时,民间文学研究也在非遗保护这项社会文化运动的不断推进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者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实践悖论,以及中国经验等问题,对非遗保护工作本身展开深入研究或批评,从而为全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和意义,矫正保护实践中的偏颇,推进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77]今天,中国的非遗保护之所以越来越强调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基本框架,[78]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路径和工作策略,并逐渐形成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同多年来以民间文学、民俗学工作者为主的一大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索是分不开的。[79]
第二,诸多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者,都积极参与到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具体实践中,在非遗相关项目的申报、考察、评审,以及保护政策和保护措施的制定、完善等方面,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中列入了长期被主流话语当作迷信而抵制的“民间信仰”[80],2008年起国家正式开始实施在清明、端午和中秋三个传统节日放假的制度,这些结果的出现,都和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得力论证与大力呼吁是密不可分的。而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是中国民俗学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常会上当选为教科文组织非遗审查机构成员。在三年任期之内(2015—2017年),该学会组织的非遗评审专家团队共负责评审了140多项由不同国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不同类型的申报材料,包括“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的申报书,圆满完成了评审任务,得到了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秘书处的赞扬。这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标志,它既提升了中国学界在国际机构和相关事务中的地位,又为学界和有关部门更有成效地进行研究与实践积累了经验。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近距离观察教科文组织与多个国家非遗保护的相关政策和实践,中国民俗学者凭借自己的专业训练和田野积累,在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文化主管部门之间,以及政府机构与民众之间,搭建了相互理解的桥梁,更加有效地推动了非遗保护工作的良性发展。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逐渐变成一种研究的视角,作为理解传统民间文学和民俗问题的重要参照,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日益强大的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指称的具体对象,同“民俗”或“民间文化”具有很大的重合性。但作为一个新概念,“非遗”的出现和普及,并不仅仅意味着用一个陌生、时髦的新词取代了老的说法,更为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反观地方或本土文化的眼光,这种眼光,使得所有相关的老传统或民间文化,都具有了“全球在地化”的丰富内涵,从而为不同事象、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和深度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加充分的前提。对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而言,这尤其是促使学科进一步拓展到更加广阔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进而从“民间”的角度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