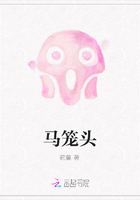
第3章 接生房的马灯
后半夜的雪片子像筛糠似的狠狠砸在窗纸上,发出密集的“簌簌”声,仿佛要将这层单薄的窗纸撕碎。王秀兰在黑暗中摸索着,缓缓摸黑穿上磨得发白的棉裤。千层底的鞋帮子早被碱土磨得发软,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鞋底与地面贴合时的绵软与无力。
外屋的马灯在寒风中“吱呀”晃了晃,昏黄的光晕随之摇曳不定。灯沿刻着的“富贵”二字在这忽明忽暗的光影里若隐若现,仿佛在诉说着往昔岁月。这盏灯是哥哥王富贵 1978年赶车时用的,如今灯油早换成了便宜的棉籽油,可凑近了闻,还能隐隐留着当年马车上特有的木头味,那是混合着木屑、草料与时光沉淀的气息。
“张婶!张婶!”急促的砸门声骤然响起,带着哭腔,划破了深夜的寂静。是西头老李家的儿媳妇,声音里满是惊慌与无助。王秀兰赶忙往棉袄里塞了块还带着余温的烤红薯,想用它驱散些寒意。暖手炉的炭火烧得正旺,红彤彤的炭火映得四周一片暖意,可即便如此,却暖不了她揣在怀里的半片蓝布——那是今天在宋家坑边捡到的。布料纹路里嵌着细小的铁锈颗粒,跟她珍藏多年的哥哥棉袄碎片一模一样,每一颗铁锈都像是一个沉默的证人。
王秀兰拉开门,刺骨的寒风裹挟着雪花扑面而来。雪地里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在白茫茫的雪地上蜿蜒,仿佛是命运留下的轨迹。她的棉鞋踩在冻硬的车辙上,发出“咔咔”的脆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路过老槐树时,王秀兰忍不住回头望去。树影在雪光的映照下,轮廓扭曲,像个佝偻的老人,怀里抱着个发亮的东西——正是白天挖出的旧马笼头。那一刻,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她想起 1980年春天,第一次听见李老汉跟宋福来压低声音嘀咕:“那外乡人埋得结实,狗都扒不开。”那时她刚把哥哥的空棉袄埋进龙王庙后,手指因为拼命扒开冻土而伤痕累累,指甲缝里还留着干涸的血渍。
产房里,油灯昏昏黄黄,光线微弱而朦胧。产妇的呻吟像漏了气的风箱,一声接着一声,充满了痛苦与挣扎。王秀兰摘下头巾,用马灯焐了焐手。这双手曾稳稳地接过三百多个孩子,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都见证过它们的温柔与力量,可此刻,在摸到产妇肚子时,这双手却忍不住微微发颤。“张婶,疼……”产妇用尽全身力气,抓住她的手腕,指甲缝里渗着血,这一幕,让她想起哥哥信里写的:“妹,要是我没回来,就去榆树屯找戴铜烟袋的汉子,他手里的笼头……”字字句句,仿佛就在耳边回响。
接生时,枕头下的黄纸不经意间滑了出来,上面画着歪扭的马笼头和七个脚印,跟周瞎子给宋家算的卦一模一样,诡异而神秘。“这是周先生给的平安符,”产妇咬着被角,艰难地喘气说道,“说能保孩子平安。”王秀兰心里一沉,想起上个月在破龙王庙,周瞎子接过银元时那虚伪的假笑:“放心,我按你说的,第七步准挖那物件。”此刻看着产妇额角不断滚落的汗珠,她突然觉得这平安符不再是庇佑的象征,倒像是一道催命符,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孩子落地时的啼哭清脆响亮,惊飞了房梁上的麻雀。王秀兰剪断脐带,借着马灯光,她的目光落在新生儿手腕上的红胎记。那胎记的形状竟跟白天那旧笼头的钩子分毫不差,宛如复制粘贴一般。她指尖猛地一抖,襁褓差点掉在炕上。记忆瞬间被唤醒,1978年腊月廿三,哥哥最后一封信里画过这个钩子,说“宋老三手里的笼头,钩子弯得像月牙”,而眼前的一切,太过巧合,让人不寒而栗。
“张婶,孩子手腕上这印子……”产妇虚弱地伸出手,眼中满是疑惑。王秀兰强作镇定,赶紧用襁褓裹住孩子:“胎记好,像戴了个金镯子,长大准有福气。”话虽这么说,可她的心却在胸腔里突突直跳,仿佛要冲破束缚跳出来。她想起宋四儿摸旧笼头时的笑,那笑容跟哥哥收的学徒小虎一模一样,而小虎,正是 1978年跟着哥哥跑运输的徒弟,自那以后,便如同人间蒸发,至今下落不明。
天亮前回到家,王秀兰从针线盒深处翻出半片蓝布。这是去年给宋福来补棉袄时剪下的,当时没注意,如今对着马灯细看,布纹里竟缠着几根马鬃,颜色跟旧笼头缰绳上的一模一样,仿佛是命运的丝线将一切串联。抽屉里的旧棉袄发出轻微的响动,她摸出藏在夹层的车票——1978年腊月廿三,榆树屯到县城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午后两点,而哥哥的死亡时间,正是中午十一点,时间的矛盾里,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富贵啊,”她对着马灯喃喃自语,声音里满是思念与哀伤,“你的魂儿,是不是就困在那笼头里?”仿佛是回应她的话语,马灯突然爆了个灯花,“富贵”二字在光影里裂成两半,像极了白天周瞎子摔旧笼头时,钩子上露出的半拉“王”字。她摸了摸口袋里的半枚铜扣,借着微弱的灯光,扣面上的纹路终于清晰——那是个“王”字,跟哥哥马车上的铜饰一模一样,这枚小小的铜扣,或许就是解开谜团的关键。
雪停了,屯子里渐渐传来扫雪的响动,铁锹与地面摩擦的声音,人们的交谈声,打破了一夜的寂静。王秀兰吹灭马灯,把半片蓝布和铜扣小心翼翼地塞进暖手炉。路过灶台时,看见昨晚给宋家的蒲公英还剩半把,叶子上凝着晶莹的冰碴。她忽然想起宋四儿摸旧笼头时,手背上渗出的血珠滴在冻土上,竟像朵开在雪地里的红梅花——跟 1978年哥哥坟前的一模一样,那鲜艳的红色,仿佛是鲜血的印记,诉说着过往的悲剧。
“张婶!张婶!”又有人拍门,这次是村长家的闺女,声音里带着急切。王秀兰整了整头巾,暖手炉的热气透过棉袄,焐着怀里至关重要的证据。她知道,今天白天在宋家坑边,周瞎子故意让旧笼头露出“王”字,高广林踢土时的慌张神情,宋福来藏铁锹时那刻意的手势,都没逃过她的眼睛。而那个红胎记的孩子,就像颗埋了十年的种子,终于在冻土初融时,冒出了带血的芽,一切真相,似乎即将浮出水面。
走出屋门,晨光正缓缓爬上老槐树的枝桠,金色的光芒洒在大地上,给万物披上一层温暖的纱衣。王秀兰看见宋福来家的烟囱冒起炊烟,烟柱笔直地升向灰蓝色的天,像根扯不断的线,连着十九年前那个没下雪的冬天。她摸了摸暖手炉里的铜扣,冰凉的金属渐渐变暖,仿佛哥哥的手正穿过十年风雪,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给予她勇气与力量。
这一晚,接生房的马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仿佛在见证着命运的流转。王秀兰在账本上郑重地记下:“三月初五,李门赵氏生男,腕有红记,状如笼钩。”字迹工整,却在“笼钩”二字上洇开了墨,像滴在雪地上的血,慢慢渗进冻了十年的土层。而冻土下的旧笼头,此刻正安静地躺在新埋的柳木笼头旁,铁锈里的“王”字,在晨光中渐渐显形,如同一张终于张开的嘴,要说出十九年前那个雪夜的秘密,揭开尘封已久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