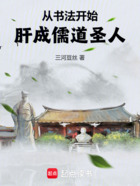
第6章 儒家修行,治经典
“那年老夫我也才十八岁,和你差不多年纪,初入书院,先生便问了我等一个问题。小沈,你也来想想看。”
孙老掌柜语意怅然,目露遐思:
“你说,这天下,有气血强横的武师,有佛爷有道士,皆可划分为九品,可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儒家修行者能独占鳌头?”
“学生不明所以。”沈言道。
“我当时也和你,是一般的想法。”
老人捻须含笑:
“后来,那位先生告诉我们,自两千年前,圣人降世,传承儒道,世间才有儒家修行者,诵读经义,积累才气。
“而后千年,儒家修行者纷纷入世,治理天下,践行圣人之道,儒道修行之法,亦与苍生气运相合。
“之后便有科举之道,应运而生。”
“科举?”
“不错!”
老学究喟然长叹:
“修行太难!
“先前跟你提到那些,武人,佛道,每上一品,都难如登天。
“唯我儒家,七品之前,并无关隘。”
沈言闻弦歌而知雅意:
“难道与科举有关?”
“正是!”
孙老掌柜点头道:
“儒家修行,要诵读《四书五经》,明悟其道理,方能积累胸中才气。
“九品治经典,八品立文庙,七品定文胆,我也就知道这一个名头,不过,小沈,当年书院那位先生,曾明确跟我们讲——
“考过童生,胸中便能生出一点才气。
“中秀才,入九品。
“中举人,入八品。
“中进士,入七品。
“只要才气积累完毕,那只消考中功名,咱们儒家的修行者,就能自然而然地提升境界。”
沈言听着,自不免悠然神往。
继而,他忽地想起一件事来:
“孙老先生,您也是一位童生......”
“然也。”
老人颔首道:
“老夫年少时,侥幸考中童生,胸中确有一点才气,大小如针尖。只可惜,日后研习经典,反复诵读,才气增长的进度十分缓慢,再加上屡考秀才不第,老夫便也绝了赶科场的念头。”
“这样说来,儒家修行者,只有考取功名,才能突破境界?”
沈言皱了皱眉。
“并非如此,只是......”
孙老先生犹豫片刻,揪了根胡须下来:
“修行境界提升,可比小沈你想的要难,不过,倒是有那么一种人,不需考童生,胸中便有才气。
“亦不用考举人,中进士,就能自然而然地成就八品,七品。
“不过这样的奇才,太过罕见,往往数十年才得见一例,以至于有个绰号——天生文曲星。”
少年闻言,若有所思。
见状,也不知道是不是来了谈兴,这位年过五旬的老人大为兴奋道:
“说起来,小沈,你可知道,谁是我龙场县,一等一的高手?”
“自是本县县令。”
沈言语气平稳,笃定地说:
“本县老爷原是经过科举,同进士出身,依老先生所言,想来是也一位七品以上的儒家修行者。”
“猜的对!”
孙老掌柜猛拍大腿:
“寻常人只知晓,县城东边有位杨武师,力大无穷,刀法凌厉,便觉得他是了不得的人物。
“他们又哪里知道,本县县令,修为早已臻至七品,那杨见龙什么东西,九品武师,真有那个斩妖除魔的本事,还至于窝在城东,收些不三不四的徒弟开武馆?”
沈言亦听过那位杨武师,此人,名声其实不坏,也不乏降服妖鬼的事迹。
于是,心中不甚赞同,少年也只恭维着笑笑。
“小沈,你要知道。
“本县老爷,何其了得,遍体才气护身,外邪不敢侵犯;张口一吐,管他什么妖魔鬼怪,皆不能抵挡这一柄唇枪舌剑!”
孙老掌柜说着,面上泛起潮红,目中绽放光彩,显然极为激动。
谈笑间,愈发兴奋,恨不得以身代之。
就仿佛,自己成了那位儒家七品修行者的县君,驾驭剑光,斩杀妖鬼!
“咳,咳,孙老,还未请教,这位县令老爷,为官如何?”
眼见老先生神采飞扬,大有一副手舞足蹈的架势。
沈言无奈,岔开话题。
“唉,这......”
老人愣了片刻,眼眸忽地黯淡,他摆了摆手:
“县令他,道德和学问是极好的。”
沈言了然。
这话言下之意,便是在说,本县县令,在为官处事上,恐怕有些疏漏。
“寻常事情,本县老爷大多不管,尽数交给手底下的差役来办。”
孙老掌柜笑笑:
“其人也很清廉,就是整日读书、赋诗,心思在修行上多放了些,倒也不能说有什么错处。
“你倒不必担心,童生试由县令主持,无非是考校些经义,文章,难的地方,在于一首五言律诗,这方面,小沈你可提早做些准备。
“不过,你的书法极好,本县县令看到考卷,必然见猎心喜,标准也会放得宽些......”
老人絮絮叨叨,反复说了些应对童生试的经验。
沈言听着,一一谢过。
至于那首被孙老先生视为最大难题的五言律诗,他倒确实有些准备。
自然不是写诗。
少年轻舒了一口气。
他简单了解过此方世界的历史。
大盛朝并非他穿越之前,所知晓的历朝历代,其中之一。
不过,上古以来,种种传说,夏商周交替,却又能和另一个世界对上。
等到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儒家孔氏圣人,孟氏亚圣,皆有其人,相继现世,相关的经学、典籍,譬如《论语》、《孟子》、《周易》、《春秋》等,无论来历内容,也都与沈言记忆中的相仿。
随后秦汉之间,亦传承清晰。
直至晋末,天下纷乱,豪杰并起。
也不知道是不是种种超凡神通的影响,历史与沈言知道的,从此再不相同。
故而,这个世界上,王朝兴替到大盛朝时——
并未经历隋唐、两宋。
纵有科举,却是在一个名为“大易”的朝代,建成制度。
少年微微摇头。
世间既无李杜白,看来,我也有机会,当上一回文抄公。
......
当日下午。
云层堆叠,天光晦暗。
孙老掌柜外出访友,沈言便只抄了半日书,就得空回来,去陈家给小陈正开蒙。
正对面,七岁大的小鬼扬着小脸儿,抑扬顿挫地背诵: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等到这部分背完,小陈正满怀期待地问:
“先生先生,我背得怎么样?”
沈言闻言,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
“不错。”
蒙学不过数日,小陈正对他的称呼,却已然从分外亲切的“沈阿叔”,变成了略带敬意的“沈先生”。
说起来,自己穿越之后,始终以读书科举为志向。
却不想,还未曾拜过老师,就先有了位学生。
也是有趣。
他略一沉吟:
“接下来,咱们温习下算法......”
与此同时,少年眉心识海内,玺印上那股浩然清气,瀑布般垂落,化成几行墨色小字:
【技艺:数术(入门)】
【进度:(3/200)】
【效用:条理清晰,擅长心算。】
......
【技艺:蒙学(小成)】
【进度:(1/500)】
【效用:识文断字,头脑清明,言语振聋发聩。】
......
两门技艺,几乎在同一时刻,双双突破小成!
沈言深深吸了口气,只觉得自身大脑,果然清醒了几分。
他在心中,默默构思了几个算式,而就在眨眼间,他便能说出答案,不需借助纸笔,只靠心算,速度仍快得不可思议。
短短三日,便在两种技能上有所进益!
沈言握了握拳。
可随即,他便冷静下来。
欣喜之情顿减。
原因无他。
想要拜入书院,所需那七两银,依然压在少年心中,如一座大山般沉重。
靠抄书?
一套二十五卷的《杨文贞公文选集》抄完,也还差着不少。
集贤堂书坊的生意又不是无穷无尽,短期内,哪来的这么多书要给他抄?
只靠抄书,怕是童生试都开考了,自己也未必能凑齐这七两银。
还谈什么考功名,中秀才?
沈言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要是有什么,能让我在三、五天内,就能直接赚到这七两银的法子就好了。
“......”
抛下种种不切实际的念头,随着目光游移,他的目光在一面墙壁上停滞了片刻,紧接着,少年狠狠咬牙:
我这也算,死马当活马医了!
......
天色将晚。
沈言向小陈正之父,陈山民辞行。
而在他走后片刻。
“爹!”
小陈正忽地跑来:
“有件事我忘了跟先生说。”
“啥子事情?”
“今天上午,我在外面玩,看到有人去找先生,拍了半天的门。”
陈山民坐在床榻上,不以为意地看了眼天色:
“也没入夜,你趁现在,跟沈家兄弟说一声,不就完了。”
小陈正摇摇头:
“先生又出门了。”
“那阿正,你还记不记得,敲沈家兄弟家门那人,长什么样子?”
“好像,好像......啊!”
小陈正鼓着脸,想了半天,忽然间拍了拍手:
“那个人脸上,这个地方,有好大一颗黑痣,上面还长了根毛!”
陈山民悚然起身,其人那张朴实的土黄色面孔,陡然间泛起血色。
这位老山户与自家妻子对视一眼:
“阿正说的,好像是赖安定,县城里有名的混不吝,嘶......沈家兄弟一个清清白白的好人,家里的,你说这地痞无赖,找他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