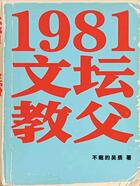
第10章 父亲的眼神
张虹告诉他,石蟆那边的知青搞了个文学社,蛮有意思的。
70年代末往后,知青群体中的地下文学团体并不罕见。
他们把笔杆子当作捅破精神牢笼的武器,摆出一副反叛的姿态,又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突破了时代美学的禁忌。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白洋淀诗群,也就是芒克、多多那帮人。
张虹和陈秀芳就是在石蟆的文学活动中认识的。
很久以后杨百川才得知,那个陷害张虹的男知青,正是那个社团的组织者之一。
这是张虹心底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
她故意提起这些事,并且装作云淡风轻的样子,是为了使男人不起疑心。
效果是有的,杨百川的确没想到石蟆的那些知青就是施害者。只是这方式太笨拙了,无异于一遍遍地自揭伤疤。
她甚至还邀请杨百川,什么时候可以和社团的同志们交流一下,把他的作品给大伙看看。
杨百川当然欢迎,他很渴望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们交流文学。他惦记着上回陈秀芳的“还不够危险”的言论,他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爆发力。
他甚至还期待了一阵儿,疑惑张虹怎么还没喊他去石蟆耍。后来又有别的事要忙,就把这茬事给忘掉了。
那晚杨百川在张虹的院坝里坐到月头偏西。二人就坐在那棵野猕猴桃树底下,从五四运动扯到三线建设。
没有光污染的夜空非常纯粹,张虹还给他指了小熊星座的方位。晚风温暖。
后来肚皮饿了,他们摸黑到地里掰了三根嫩苞谷,甩进灶灰里焖。
等到山坳里狗都懒得叫了,他攥着张虹给的虎头牌铁皮手电,踩着露水到公社过夜。
第二日,天麻麻亮时,他托人把手电捎给张虹,就径直回了厂。
刚打开家门,就看到母亲韩家书手里攥着一张白纸,立在客厅中央,端着播音员的腔调念纸上的内容,只是把“学”念成了“xio”,“书”念成了“su”:
“高等学校学生入学通知书……”
幺妹杨百云站在一旁,笑眉笑眼地望着母亲:“妈,快念!”
杨清淮在沙发上正襟危坐,嘴里叼着一截烧了一半的烟,笑眯眯地望着母女俩。
杨百川推门时,韩家书停下来,举着手里那张白纸:“哎呀,百川回来了,快,你幺妹的通知书!”
百云催促道:“妈,你搞快点念嘛!”
“高等学校学生入学通知书。经省教委批准,杨百云同志入w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是住校生。报到时间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七日,请凭本通知到校报道!”
就像一个预言。
杨百川给张虹说的安慰话,竟然在幺妹身上应验了。
幺妹考上了汉大。
这所在后世入选985、211的大学,是HUB省最好的学校之一。在日后还出了些很有钱的校友,大米集团的创始人雷君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给汉大捐了13亿。
幺妹前途无量啊!
杨百川笑着走过去,摸了摸幺妹的脑袋。
韩家书拍了下他的胳膊:“到时候你要送你幺妹去学校哦。”
那太好了!穿越前,杨百川在鄂北念大学,某个国庆去汉城耍过一趟。不知道这个年代的汉城是什么样子。
身后突然传来杨清淮幽幽的嗓音:“杨百川,听你妈说,你收到封燕京寄来的信?”
韩家书也调换了话头:“就是,我还是从老孙那儿晓得的。这个娃儿,有好事都不跟妈老汉说!好像是那个啥子七月还是八月寄来的,对不对?”
这个老孙,真是个敞嘴巴……
杨百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啥子七月八月,人家是《十月》。”
杨清淮把手里的烟头往缸里一摁,搓了搓手:“信呢?给我看一眼。”
杨百川还没来得及放下挎包,便顺手从包里取出信,将原稿抽出来,单把两张印着“十月”的信纸交给父亲。
他面上十分腼腆,心里却得意昏了。老登,你儿子牛吧!
百云伸着脖子,扯了扯父亲袖口:“给我瞄眼噻,写的啥子?”又扭头看杨百川,“哥,《十月》是啥子?”
“就是个杂志社,燕京那边的。”
杨清淮又点了根烟,在嘴里狠狠地叭了一口,把信纸递给百云:“很不错嘛,再接再厉。”
他一愣。无论是这四十多天还是原身二十多年的记忆,父亲夸自己的次数掰着指头都数得清。
他意识到,自己能接到《十月》的回信,对父亲而言也是一件非同一般的事。
他从那张干瘦、黝黑的脸膛上看到了一丝期待的光亮,却也被经年累月的冷峻所掩盖着,十分模糊。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百川就整天窝在家里改稿。
原先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给《十月》寄稿子,竟真的中了,就不得不用十二分的认真打磨这篇稿子。
市作协的信封是在三天后来的。
既然已经收到过《十月》的改稿信,再捏着这张联谊会的邀请函,手倒是不抖了。
老孙是反应最大的那一个。他看到信封上印着“临川县作家协会”的字样,惊抓抓地叫唤:“杨老师,你是作协会员啦?!”
杨百川连忙摆手,解释说自己只是去参加活动的。
他撕开信封。邀请函上讲,从8月20号到30号,渝城周边几十个县的青年作家将齐聚文联系统的人民招待所,期间食宿全包,还有省里来的老编辑讲课。
入选并非意料之外,本来就是周明远推荐的,等于提前筛过一道。
但杨百川还是很兴奋的。
这种联谊会在“纯”文学圈子里是司空见惯的,也有些别的名目,比如什么改稿会、研讨会、诗会等等。
其实就跟公费旅游差不多,把一群作家凑在一起,开开会吃吃饭喝喝酒,顺便在当地耍一耍。
吃饱喝足耍高兴了,各自回去写些东西出来,再登到杂志上或者结集出版,就算没白来这一趟。
杨百川穿越前的那个时代,有不少县为了带动当地旅游,常跟大刊物合作,拿地方财政的钱支应着,开诗会文会,也是这个路数。
杨百川这回参加的,是青年作家联谊会,相对来说还是单纯些,以改稿、交流为目的,没那么多花哨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