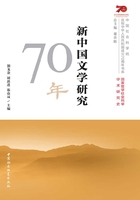
二 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
正确的思想路线确定之后,组织保障就是决定性因素。文化管理与科研部门在课题组织、传播平台、体制建设、资料编纂等方面,积极组织策划,开创崭新局面,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
(一)专业研究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缺乏组织协调,学术研究各自为政,多处在松散游移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组织建设,整合学术力量,逐渐形成三大研究系统。
一是社会科学院系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中心。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专业机构,最初挂靠在北京大学,1955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64年,文学研究所苏东组、东方组、西方组分出,与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合并,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1979年,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骨干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改称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文学专业研究机构,荟萃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遵照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总体目标,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文艺理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古典文献学等研究领域,勇于探索,求实创新,撰写出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研究专著,培养出一代代专家学者,为繁荣发展我国文学学科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发挥自身优势,也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形成各具特色的学科。譬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以明清小说研究为特色,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以红色经典研究为特色,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以柳宗元研究为特色,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以浙江文学研究为特色,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以民族交融研究为特色,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以敦煌文学研究为特色,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以宋代文学研究为特色,等等。
二是高校系统,以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为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育部对全国各类型大学进行全面的院系调整,形成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齐头并进的基本格局。截至2018年3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79所,相当一部分院校都建立了中国文学学科。其中,“211工程” “985工程” “双一流建设”大学具备较为齐全的中国文学研究力量。譬如复旦大学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有文艺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有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等等。部分高校还逐渐形成一批富有特色的中国文学研究“重镇”,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教材是高校的最大亮点,在三大体系建构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其他系统,以文联、作协、文化部所属各类研究机构为主,也包括新闻出版行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都设有研究机构。如作协自成立之初至1956年9月,设有古典文学部,也曾短暂组织参与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文学遗产》编辑部最初就设在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后来,这两大机构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如鲁迅文学院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培训青年作家。1950年成立,最初叫中央文学研究所,1954年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84年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此外,还有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各地的鲁迅博物馆、杜甫博物馆、三苏祠等著名文学家的纪念场所,负责专业展览,协调宣传工作。中国文联下辖各文艺家协会,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文化部下属相关事业机构,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就有《红楼梦》研究所、戏曲研究所、文化研究所等,其工作性质,也多与中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
(二)学术传播平台
20世纪前期,虽然一大批出版机构热衷于出版中国文学基本典籍与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但总的说来,还没有形成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图书出版行业发展迅猛,原典整理与研究成果的出版、传播、评价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大体系的建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单位以及各地方出版社、著名高校出版社,还有不同种类的专业出版社等,纷纷组织相应的系列整理与研究工作,而且很多编辑也兼具文学研究工作者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学术著作的出版日益兴盛,历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得到系统整理,中国文学研究论著,包括普及性著作(选注、选译、选讲),得以大量出版,深受读者欢迎。近年来,中国图书出版量高居全球榜首,其中就包括与中国文学相关的各类出版物。譬如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龙头,七十年来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影响极大。就以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元诗》《全元文》《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明散曲》《全清词》及《文选》《文苑英华》《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大型文学资料总集或经典文本,或重新校点整理,或系统编纂,已经或将陆续问世,蜚声海内外。
现代中国学术性报刊的兴起,也为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公共平台。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重要党报都开辟有文艺评论专版,《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评论、研究性杂志,多具有全国性影响。还有《人民文学》《诗刊》《当代》《十月》《收获》《钟山》《花城》等收录创作的专刊以及高等院校的学报、各省市社科联主办的人文社科类杂志等,在组织开展文学评论、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由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三份大型学术刊物《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中国文学年鉴》。
《文学评论》创刊于1957年,办刊方针非常鲜明:一是“中外古今,以今为主”,二是“百家争鸣,保证质量”。其选题范围包括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作家作品评论等。六十多年来,《文学评论》组织开展了很多引领潮流、富有价值的学术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关于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思潮和学术流派,关于中国文学经典文本重新解读的文章,评述了国内外新的文艺思潮、文艺观点和创作流派。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评论》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开展讨论。《文学评论》还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专门组织发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小说、电影、话剧和诗歌研究方面的文章,对三十年来既有重大成就、同时又充满曲折和失误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总结。同时,对于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文学评论》也给予了积极关注,如对《班主任》《沉重的翅膀》《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小说作品,及时组织相关讨论,起到鼓励创新和开拓的作用。新世纪、新时代,《文学评论》将继承学术传统,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发挥好学术平台的助推作用。
《文学遗产》是唯一的国家级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创办于1954年,也组织参与了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拨乱反正前后,《文学遗产》与《文学评论》一道,组织全国文学界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文学研究队伍、研究状况及课题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确定新的科研发展方向,在促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以及拓展学术研究空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创办于1981年,集学术性、文献性、资料性为一体。后来,该刊增加创作部分,改称《中国文学年鉴》。长期以来,这份“年鉴”是国内唯一一本涵盖从创作、论争到批评、研究的大型文学年刊,客观地记录每年度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进展过程和重大事件,真实地反映每年度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成果,聚焦文学热点,展示文学成就,为人们了解年度文坛情况,提供全方位信息。
近年来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加速趋势。“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文明戏、广播、电影的相继出现,传统印刷媒体独步天下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当时,除了“看”的文学革命,“听”的文学革命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而今,文学的看与听,依然平分秋色。据2018年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我国至少有三成的国民有听书的习惯。随着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互联网异军突起,中国文学研究开始走出纯粹的纸媒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联合推出学术期刊数据库,努力在资源共享方面,理顺关系,为广大读者服务。
当前,从数字化到智能化,信息革命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固有的学术生态环境,包括研究方式、传播方式,都在发生重大变化。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当重视中国文学研究的全媒体建设与媒体融合发展,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在传播方面的新方向与新追求。
(三)学术资助机构与民间学术团体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后,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国家艺术基金以及各省部级机构设立的专项经费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研究工作的开展。这些专项资金,不仅支持了专家开展系统的研究,也包含着学术的引导和研究成果的评价,意义越发凸显。
综合性、专业化的文学研究学会相继成立,也为学者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成果的传播,提供良好平台。这些学会,有的是综合性的,如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有的是按照文体设立的,如中国词学研究会、中国散文学会等;有的是按照时代设立的,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有的是按照地区设立的,如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也有的是以作家名义设立的,如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杜甫学会、中国李白学会、中国鲁迅学会;还有的是以专书名义设立的,如《文选》研究会、《红楼梦》研究会等。很多学会还创办专刊,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鲁迅研究会有《鲁迅研究月刊》等。
(四)资料编纂工作
从全国范围看,这项工作浩繁博大,成果众多。在这有限的篇幅内,很难面面俱到。这里,略以文学研究所的资料编纂工作为例,尝鼎一脔。
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整理。1960年年初,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到文学研究所考察工作,明确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研究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1965年,周扬再次就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重心提出建议,强调搞“大中型”的研究项目,认为这是关系“文学研究所的存在”的问题。
在文学理论方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苏东组有计划地翻译介绍了古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又制订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参考资料。
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1954年郑振铎召集吴晓铃、赵万里和傅惜华等人主编影印《古本戏曲丛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目标是编纂一部系统完备的中国古代戏曲总集。这套丛书的编纂,跨越六十多年的岁月,今年终将圆满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献上厚礼。此外,《古本小说丛书》《中国古典小说总目》等,也是郑振铎最初策划,并由文学研究所集体完成的。
现当代文学方面,由文学研究所牵头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思潮流派、社团资料;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总目、总书目、作家笔名录等。这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资料丛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文学研究所还联合复旦大学、杭州大学、苏州大学等三十多家单位协作编辑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凡八十余种,两千多万字。其中,作家研究专集选编有作家生平与自述、生活照片和手稿照片、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以及作家创作年表。已出版的长篇小说研究专集则收有出版的长篇小说目录、对重要长篇小说的评论与争鸣文章等。
此外,荒煤、冯牧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的当代部分,作家出版社邀请名家分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林非主编的《当代散文大系》,谢冕、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新诗萃》,谢冕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谢冕与孟繁华合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谢冕与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南开大学张学正等主编的《1949—1999文学争鸣档案》等,均深具选家眼光,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